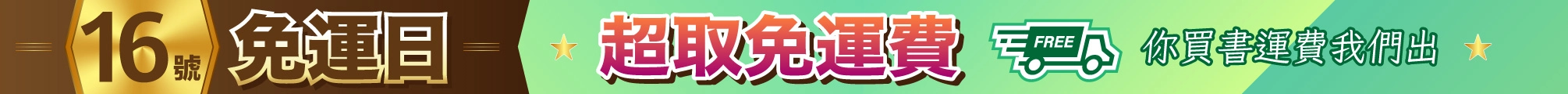攀向自由:波蘭冰峰戰士們的一頁鐵血史詩
- 作者:柏娜黛.麥當勞(Bernadette McDonald)
- 出版社:臉譜
- 出版日期:2021-01-05
- 定價:599元
-
購買電子書,由此去!
分類排行
-
颶光典籍五部曲:風與真實(上下冊套書,限量附贈寰宇磁鐵徽章「西兒」款)
-
都市傳說第三部1:神奇扭蛋機(限量隨機透明書籤版)
-
指揮使夫婦今天怎麼了?(限量作者親簽贈品版套書)
-
無法說出口(暢銷言情名家鏡水糾葛難言祕戀之作套書,讀者等待多年終於登場!)
-
禁忌之子(一出道即入圍日本書店大獎,日本怪物級新人醫師作家登場!)
-
火槍騎士與木偶巫師(布蘭登・山德森、喬治・R・R・馬汀同聲盛讚!作品熱銷全球700萬冊,備受國際奇幻大師肯定的槍火魔法冒險故事集)
-
克蘇魯神話VI(完結篇):未知(精裝)
-
三體前傳:球狀閃電
-
魔女的原罪(日本最受矚目法庭推理鬼才,現役律師給社會的反思與救贖)
-
都市傳說5:裂嘴女(十周年機密檔案限量典藏版)
內容簡介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2020年全新山岳文學書系meters 作品|
「戰爭的殘酷鍛鍊出他們的堅忍與毅力。
所有登山菁英背後的故事相去不遠:歷史強化了他們的身體與心智。
他們不單是登山家——他們是『波蘭』的登山家。」
出版後囊括全球山岳、自然文學類大獎
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得主.加拿大山岳文學名家柏娜黛.麥當勞經典巨著
記錄下於國族苦難後浴火而出,攀上世界巨峰,一群波蘭傳奇登山者們的冒險、生命與心靈,以及波蘭的榮耀與悲傷
「這麼多年來最重要的山岳寫作,終於問世!」
——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Boardman Tasker Prize for Mountain Literature)
「這是一個縱橫於巔峰峻嶺間、周旋在官僚政治中的故事,波瀾壯闊,扣人心弦,
揭開喜馬拉雅攀登的黃金年代,悲壯中,難掩神采。」
——英國登山教父 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
經歷二戰及德蘇強權的暴虐蹂躪後,波蘭在極權高壓統治下百廢待舉。但在這時代裡,一群登山家橫空出世,不只與惡劣政權共生共存,更在資源極端缺乏下,展現無與倫比的能力與野心,打造出世界一流的登山隊伍,稱霸國際。在本書中,二度獲得「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的知名山岳文學作家柏娜黛.麥當勞,記載下這群登山家的生命故事,也帶我們進入他們的內心與意志,見證他們如何在苦難中締造傳奇,在群山上尋得失落的自由。
▍經歷納粹清洗、蘇聯高壓統治,奄奄一息的波蘭從「登山」窺見通往世界與自由的航道
一九三九年,納粹與蘇聯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後,聯手瓜分波蘭,一邊將波蘭人民送進集中營或立即處死,一邊將波蘭「罪犯」做為奴隸剝削,六年間超過六百萬波蘭人民死亡,約當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二戰過後「和平」降臨,蘇聯美其名「解放」了波蘭,實為讓波蘭從此陷入蘇聯傀儡政權的高壓統治。
波蘭的登山風潮很早萌芽,二〇、三〇年代就有「山岳俱樂部」的創設,大戰之間仍勉力運作。而就在戰後經濟敗壞、民不聊生,民主化的期盼也落空之餘,共產政府從五〇年代中期開始,竟願意讓登山家們前往海外登山,原來是希望透過登山家在國際揚名,為祖國爭取光采與名聲。即使面對道德兩難,許多登山家們為了追尋自由,仍選擇與政權共生共存,前往世界各地挑戰高峰,幾年之內,世界各地的高峰都成為了波蘭的天下。
由於經濟蕭條,登山設備在波蘭幾乎無從購得,但波蘭登山家仍勉力從原料開始組合各式的登山設備——從布料、拉鍊開始手縫服裝,請鞋匠手製登山靴,請打鐵舖量身打造冰斧……,而登山家們也在國內做苦工、彩繪煙囪,或者趁出國走私威士忌、舶來品來籌措經費,為的就是前往遙遠國度的峰頂,呼吸自由的空氣。
▍一九七〇至九〇年代——波蘭「冰峰戰士」們的喜馬拉雅黃金時代
在經過六〇年代於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的遠征熱潮,波蘭在國際登山界開闢新領域的時機已然成熟,在七〇、八〇年代,波蘭登山家們開始朝喜馬拉雅山區挺進——即使各國已在五〇、六〇年代陸續登上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波蘭登山家們仍決心急起直追,更要超越紀錄——在艱難的冬季攀登,不戴氧氣瓶的無氧攀登,或者創造無人攀登過的困難新路線,而他們也真正在這二十年間不斷締造驚人的輝煌傳奇,被世界稱作「冰峰戰士」(Ice Warriors)。
本書就將從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波蘭登山家出發,講述這群冰峰戰士以及這個黃金年代的故事——
汪達.盧凱維茲(Wanda Rutkiewicz,1943-1992)
她是第一位登上聖母峰的歐洲女性,更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同日登上世界舞台。勇氣十足,拄著柺杖也要挺進K2峰,生涯充滿野心,重塑了登山界的性別政治,是波蘭黃金年代最耀眼的一顆巨星,被認為登山成就遠遠領先她的時代。但在光鮮的背後,她的生命充斥著孤獨與悲傷,也在登山界裡擁有兩極評價。即便如此,她於一九九二年挑戰干城章嘉峰上失利喪命,仍震撼了登山界,公認從此失去了一個偉大的登山家。
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 1947-)
出身書香世家的他,登山技巧出類拔萃,決策務實果斷。而與許多登山嘉追求巔峰紀錄不同,歐特克的登山風格饒富哲學氣質,不莽撞、不執著,卻也創下眾多經典的傳奇攀登紀錄,被譽為是「登山界的思想家」。他曾表示登山是揉合運動、藝術與神祕信仰等諸多元素融鑄成的生活方式,需要駕馭靈感。二〇一六年,他獲頒世界金冰斧終身成就獎。
亞捷.庫庫奇卡(Jerzy Kukuczka, 1948-1989)
「在無數人心中,他就是勇氣與無畏的象徵。」亞捷.庫庫奇卡不只完攀世界上十四座八千公尺巨峰,而且有十座是自闢新路線,四座是在冬季攀登,更有一座是獨攀,締造了無人撼動的世界紀錄,義大利登山皇帝梅斯納爾更稱他為「世界最偉大的奇才」。但他卻於一九八九年挑戰洛子峰南壁意外墜落兩千公尺喪命,波蘭舉國哀悼,甚至各地學校紛紛將校名改為他的名字以紀念這位波蘭傳奇。
以這三位登山家為首的波蘭登山者們,不只勇於挑戰不可能,展現驚人創舉,他們的生命故事也是世界珍貴無比的遺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政治與山岳文化,更深刻體現了「登山」的本質及精髓。
▍是締造傳奇的黃金年代,也是傷亡慘重、壯烈犧牲的鐵血年代
但在波蘭接連創下傳奇紀錄的背後,登山家們的犧牲也重創了波蘭登山界。在這幾十年內,百分之八十的極高海拔登山菁英喪命於峰嶺上。隨著登山家們的消逝,波蘭損失了大批登山好手,加上經濟水平提升後,海外登山的魅力不再,資本消費主義讓人們的慾望轉向,也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面貌與心靈。
「魔術般華麗的黃金年代終究是結束了,好些頂尖的登山家隨風而逝。但他們的遺產,他們累積遺產的傳奇手段,依舊迴盪在空氣稀薄的世界絕頂;不想爬到那樣高的人、不願甘冒奇險的人、無法企及那種偉大的人,難窺堂奧。但他們仍然在,等待有緣人。」
本書作者柏娜黛.麥當勞是世界知名的山岳文學作家,也是登山家、電影製作人與策展人,她曾參與創立加拿大班夫藝術與文化中心,任職長達二十餘年,並曾任國際上最具知名度山岳影展「班夫山岳影展」的總監。她在汪達逝世前,才當面邀請汪達前往班夫影展擔任嘉賓,而在兩年後前往波蘭卡托維茲策畫影展時,也結識了一群曾在波蘭黃金年代締造傳奇的登山家們,並更深入聽聞了他們那些逝去朋友們的故事,燃起了她對波蘭黃金年代的好奇。因此,她決定親自挖掘、記錄下波蘭稱霸喜馬拉雅登山界的往事,剖析這群登山家的心靈,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們不畏風險,犧牲性命也要締造出如此輝煌紀錄?
經過數年的大量採訪與資料收集,本書出版後好評不斷,更獲得包含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Boardman Tasker Prize for Mountain Literature)等諸多全球山岳、自然文學類大獎。本書的中文譯本出版,也將是第一次將世界上最重要的這段登山史,完整而深刻的呈現於中文讀者眼前。
【各界推薦】
王迦嵐 健行筆記總監
伍元和 山岳愛好者
江秀真 全球華人女性首位完攀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李明璁 作家、社會學家
呂忠翰 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張元植 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雪羊視界 知名登山部落客
——推薦
「這麼多年來,最重要的山岳寫作,終於問世!」
——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Boardman Tasker Award for Mountain Literature)
「重量級巨作,掀開喜馬拉雅登山史的全新篇章。」
——萊茵霍爾德.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義大利登山皇帝,十四座八千公尺顛峰全攻略記錄開創者
「這本書發人深省,波蘭登山巨星,在她的筆下,展現無比動人的魅力。」
—— 艾德.維斯特斯(Ed Viesturs),著名美國登山家,創下無氧攀登十四座八千公尺巔峰紀錄
「聚光燈投在身手不凡的『絕頂』高手與他們的出生入死的冒險經歷,重新喚起世人的記憶,榮耀還諸登山名家。柏娜黛.麥當勞的表現,讓人激賞!」
—— 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著有《生命的尋路人》(The Wayfinders)、《靜謐的榮光》(Into the Silence)
「標誌登山界最高理想的作品,精彩動人!」
——登山雜誌《緊握》(Gripped)
「作者的生花妙筆描繪出近年來最引人入勝的登山佳作,活力、鮮明,細膩掌握時代特色,勇闖顛峰,在群山峻嶺間屢創佳績的各路英雌好漢,躍然紙上!」
—— 《登山》(Climb)雜誌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山岳文學書系 meters——
現代人,也是登山的人;或者說——終究會去登山的人。
現代文明創造了城市,但也發掘了一條條的山徑,遠離城市而去。
現代人孤獨而行,直上雲際,在那孤高的山巔,他得以俯仰今昔,穿透人生迷惘。漫長的山徑,創造身體與心靈的無盡對話;危險的海拔,試探著攀行者的身手與決斷;所有的冒險,顛顛簸簸,讓天地與個人成為完滿、整全、雄渾的一體。
「要追逐天使,還是逃離惡魔?登山去吧!」山岳是最立體與抒情的自然,人們置身其中,遠離塵囂,模鑄自我,山上的遭遇一次次更新人生的視野,城市得以收斂爆發之氣,生活則有創造之心。十九世紀以來,現代人因登山而能敬天愛人,因登山而有博雅情懷,因登山而對未知永恆好奇。
離開地面,是永恆的現代性,理當有文學來捕捉人類心靈最躍動的一面。
山岳文學的旨趣,可概分為由淺到深的三層:最基本,對歷程作一完整的報告與紀錄;進一步,能對登山者的內在動機與情感,給予有特色的描繪;最好的境界,則是能在山岳的壯美中沉澱思緒,指出那些深刻影響我們的事事物物——地理、歷史、星辰、神話與冰、雪、風、雲……。
登山文學帶給讀者的最大滿足,是智識、感官與精神的,興奮著去知道與明白事物、渴望企及那極限與極限後的未知世界。
這個書系陸續出版的書,每一本,都期望能帶你離開地面!
▍詹偉雄——策畫.選書.導讀
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擔任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文創產業創業者,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hopping Design》、《Soul》、《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
退休後領略山岳與荒野之美,生活重心投注於山林走踏與感官意識史研究。2019年協助青年登山家張元植與呂忠翰攻頂世界第二高峰發起「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目前專職於文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行、寫作。
目錄
登山與現代──meters書系總序│詹偉雄
推薦序 夜空中最亮的星│張元植
推薦序 喚起攀向自由的下一代│呂忠翰(阿果)
推薦序 要想獲得勇氣,必須求之在我│伍元和
導 讀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波蘭的,也是台灣的│詹偉雄
序曲
第一章 登山杖與釘鞋
第二章 登山政治學
第三章 沒有邊界的攀登者們
第四章 專注
第五章 聖母峰上的帽子戲法
第六章 戒嚴下的團結
第七章 結伴?孤身?
第八章 第三者
第九章 受苦的藝術
第十章 悲慘群山
第十一章 鐵打鋼鑄
第十二章 喜馬拉雅玫瑰經
第十三章 巨星殞落
第十四章 夢想篷車隊
第十五章 山徑人蹤滅
第十六章 最寂寞的皇冠
尾聲
跋
附錄 波蘭喜馬拉雅登山大事編年
附錄 完攀八千公尺以上高峰的波蘭登山家
內文試閱
▍序曲 Prologue
我始終覺得波蘭人天賦異稟。也許,特異過頭。但這天賦,是做什麼的呢?
——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
她站在吧台邊,手裡握杯啤酒。她的溫暖迎面朝我撞擊而來。身邊圍著一圈粉絲的她,正在講故事——我想是登山吧。她不時用飽受天氣蹂躪的雙手強化敘述,但真正飽含世故的卻是她的臉龐。義式咖啡似的深色眼眸,被好些線條裹住,那是爽朗的笑聲與高海拔罡風刻畫出的痕跡。桀驁的栗色波浪鬈髮,亂糟糟的蓋住寬闊的前額。笑容如此燦爛,完全融化了她那強硬的波蘭下顎。
我走近酒吧,她看了我一眼,「嗨,歡迎。來杯啤酒吧。我是汪達。」
我當然知道。為了跟汪達.盧凱維茲(Wanda Rutkiewicz)見上一面,是我飛越大半個地球,來到蔚藍海岸山上參加電影節的緣故。昂蒂布(Antibes)很棒,但十二月則未必。
我們放棄當晚放映的電影,站在大廳的酒吧邊,暢談、大笑,議論我們共同的好友軼事。我們談到亞捷.庫庫奇卡(Jerzy Kukuczka),波蘭首屈一指的登山家,兩年前死於洛子峰(Lhotse)南壁。這個溫和的大個頭,是汪達最親密的戰友。我見過他兩次,一次在加德滿都,他攀登干城章嘉峰(Kangchenjunga)後凱旋歸來;一次在北義大利,我們共享午餐,足足吃了三小時。還有其他陪客:克提卡.歐特克(Kurtyka Voytek)、寇特.狄姆伯格(Kurt Diemberger)、吉姆.庫倫(Jim Curran)。好多故事。好多笑聲。好多啤酒。
站在汪達身邊,我頗訝異她的嬌小。很難想像她竟然能揹起沉重的登山裝備。她很苗條,幾至纖細。只有下顎堅實異常。還有她的雙手,筋肉虯結、飽經風霜。
她的穿著也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原本以為這位波蘭之星的打扮,會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復古、襤褸、優雅,不確定,但總該表露點什麼。沒想到她卻穿得隨便,刷毛、棉質,也不管搭不搭調。當然,她剛從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遠征返來,壓根沒時間喘口氣,自然不可能打扮好來參加派對。
夜晚舒展,我揭露我的醉翁之意:想請她到班夫(Banff)山岳電影節,擔任開幕致詞嘉賓。我是電影節的執行主任,這是我的工作。她很熱心,一諾無辭。我們瞥見瑪麗安.費克(Marion Feik),類似她的保母兼經紀人,在附近閒晃;三個人就這麼聊起來了,決定讓汪達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份造訪加拿大。
兩個小時之後,觀眾從戲院潮水般的散去;我們還是待在酒吧裡,加滿飲料,空蕩蕩的大廳,找了幾把襤褸的皮椅坐定。
「現在,柏娜黛,我要告訴妳我的計畫。」汪達說,「我稱之為『夢想篷車隊』。」
「聽起來很有意思。」
「我想成為爬遍十四座八千公尺巔峰的女性第一人。妳知道我已經爬過八座,我想征服其他絕頂……」
「別人做得到,妳當然也做得到。」
「……在未來的十八個月內。」
「什麼?妳是認真的嗎?我覺得這不可能。」
「不會,不會,是有可能的,因為這樣一來,我就能一直維持我的高度適應力,妳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座接著一座盡快的爬。」
我放下杯子,身子前傾。「汪達,說真的,妳不能這樣輕率——這個計畫太危險了。妳有沒有好好的跟別人討論一下?別的登山家怎麼說?」
我盡全力反對。儘管我沒有攀登過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但非常確定這個計畫完全不合理。此舉,前無古人。登山家總是想要蒐集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登頂紀錄,但只有萊茵霍爾德.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與亞捷.庫庫奇卡完成壯舉。何苦這麼急呢?我問道。可曾考慮疲憊這個因素?
瑪麗安投來一個求助的眼神。她先前自然聽過反對意見。許多次。我從她的眼神可以分辨,她是贊同我的。但是計畫並不是由瑪麗安策動。這是汪達的主意,而汪達很焦急。
「我都快五十了。」她說,撥開垂在眼前的頭髮。「我的速度越來越慢,高度適應不像以前那樣輕鬆。我得擬定策略,一群一群的爬。我辦得到的,妳知道。只需要一點運氣,天氣不要太糟就好。」
我不再反對。很明顯的,跟汪達多爭無益。
我們同意接下來的幾個月,在她遠征的空檔保持聯絡。她回報最新動態,我啟動宣傳機器,預告她即將蒞臨加拿大。
一九九二年,翌年春天,她從加德滿都寄來一封航空郵簡,就在她準備攀登干城章嘉峰之前。這會是她第九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她滿懷自信、態度果決,渴望畢其功於此役。我只能祝她幸運。
但汪達並未返來。
...
兩年之後,我來到波蘭的工業心臟,卡托維茲(Katowice),協助策畫影展。活動大獲好評,數百名熱情的觀眾爭相走告,觀賞電影之餘,還重拾登山同好之間的聯繫。大禮堂內活力四射,渾然忘卻外頭波蘭的陰鬱苦寒。在這個冰冷荒廢的舊工業重鎮,竟然有這樣多的登山愛好者,著實讓我訝異。這夥山友外表堅強,放蕩不羈,魄力十足。我看得興趣盎然。
影展接近尾聲,好些登山愛好者邀請我去波蘭山岳協會俱樂部小聚。這是一棟潮濕寒冷、骯髒晦暗的建築;但室內卻是溫暖、明亮,有喝不完的伏特加,熱鬧的程度不輸搖滾演唱會。
好些攀登喜馬拉雅山平安倖存的登山家都出席了,包括扎瓦達、維利斯基、哈澤、利沃夫、馬傑爾、鮑洛斯基等人。我知道他們輝煌的歷史,覺得他們個個獨樹一格,高瞻遠矚。他們在崇山峻嶺間,另闢前人不曾涉足的蹊徑,悍然無懼;攀登地球最高的峰頂,迎向(經常還成功克服)殘酷無情的寒冬,信心堅定,不曾有半點猶豫。
但是,房間裡卻有明顯的悲傷情緒。在他們深愛的高山裡,好些朋友犧牲了性命;他們的名字總是被一再提及,讓我無法聽而不聞。亞捷.庫庫奇卡是其中之一。汪達也是其中之一。我表達對這兩人的敬佩,也暗自慶幸認識這兩位登山界的傳奇,儘管,相遇是那樣短暫。有些人點頭微笑贊同,卻也有些異議,特別是關於汪達。「妳太過欣賞她了,」其中一人說,「她還有妳未曾得知的一面。冷硬、精於算計。她的確很強悍,像一頭野牛。」
我抗議。她當然要強悍,否則,在那般極端的環境裡,何以存活?「是啦,這是真的。」他揪了揪讓人過目不忘的八字鬍,「但她用力過深,總是在鬥,難相處,好勝心又強。我們愛她,偏偏她又不知道,一直以為她是獨自奮戰,把我們推得遠遠的。但我們其實是愛她的。」
「那麼庫庫奇卡呢?」我說,「他也是生性好鬥嗎?」
「不,不,亞捷沒時間跟別人爭鬥。他忙著爬山。一度,他有點分心——那場競賽——妳記得吧?跟萊茵霍爾德.梅斯納爾。兩個人都想率先完成十四座八千公尺的全攀登紀錄。但他回來了……完成他的挑戰之後,又回到真正的攀登——挑戰那面仰之彌高的山壁。」
「也害他丟掉性命。」我反駁說。
「這倒是真的。但是他是真正的登山家。波蘭第一。」
他們講起歷史的風雲變幻,講起共產黨統治那段瘋狂但美好的歲月;那時中央政府瞭解也願意支持登山家——至少頂尖的幾位絕無後顧之憂。他們興致勃勃的議論當時的另類職業專長,如何支持他們完成攀登喜馬拉雅山的夢想。他們的工作多半是清理或者彩繪工廠煙囪。滑溜溜、顫顫巍巍的煙囪,構築卡托維茲的天際線。這是很危險的工作,不僅容易失足,工作環境對身體也是毒害甚巨。有時,他們會放低聲量,從曖昧的態度來判斷,應該是議論走私——一度獲利驚人。但是,時代變了;現在的他們只覺得自己被搖搖欲墜的波蘭自由市場經濟棄之不顧。
直到凌晨三點,我們終於離開俱樂部。即便我們踩在潮濕、沒有路燈的街上,派對的溫暖依舊迴盪在我們心中,完全無感於刺骨寒風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回到加拿大,我還是經常想起卡托維茲的夜晚。我珍惜偉大登山家成就的動人故事、即將要開展的計畫與失去的摯友。但也不免狐疑汪達以及其他登山家,何以有這樣兩極的評價?某些登山英雄可能比我的想像,要來得要更加複雜。尤其是汪達,我親身感受到的溫暖,實在很難跟隨後湧現的謎樣形象連在一起。我老是會把當晚聚會感受比擬成守靈——一種懷舊的情緒,哀喜參半的悼念一段獨特的歲月:攀登喜馬拉雅的黃金年代、一個消逝不復返的年代。
我想起波蘭苦難的現代史。六十年來,飽受暴力威脅與鎮壓、大規模的反叛以及奇蹟式的重生。精誠團結的登山界,是怎麼跟這種惡劣的政權共生共存,展現無與倫比的能力?又是怎麼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喜馬拉雅登山隊伍?種種現象著實費解。是艱困的時局造就他們的野心?或者只是強化他們原本就有的桀驁與不屈?訓練他們自虐自強?
如今,波蘭再次歷經巨變,幸好這一次應該是朝正向發展。我不知道波蘭的登山家怎麼因應。優渥的生活會強化他們在山上的表現?或者引他們分心?
這些問題勾起我的好奇,在卡托維茲之夜許久許久之後,依舊渴望一探究竟。最後,我決定挖掘得再深一點——挖進波蘭稱霸喜馬拉雅登山界的往事,挖進黃金年代登山家的人性矛盾。哪種形象才是真正的汪達?她能不能引領我走進這批「絕頂」高手的內心與意志?儘管受到國家的形塑,但他們可有能力突破這層限制?
這個故事就是記載他們翻越高山,迎向自由的奇異旅程。
————
▍第一章 登山杖與冰爪 Crutches to Crampons (節錄)
祝你通往絕景的小徑,蜿蜒曲折、危險寂寞;祝你的山勢拔起,直插雲霄。
——愛德華.艾比(Edward Abbey),《祝禱文》(Benedicto)
前路多艱。大大小小的礫石散落腳下,歹毒的結冰面陰森森的藏在薄薄、鬆軟的砂層間。陰暗的巴瑞都河(Braldu River)從地下深處傳出怒吼聲,大地都為之震動。一個形容枯槁、臉頰凹陷的女人,一拐一拐的往前行,痛苦籠罩著她的黑眼珠。她停下腳步,往石面上一靠,碎屑簌簌掉落,伸手往口袋裡一探,摸出兩顆止痛藥,往乾裂的嘴唇裡一扔。
時值一九八二年。汪達.盧凱維茲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喜馬拉雅女性登山家,擅長跟女性搭檔。這次是夏季攀登:她找來十二位頂尖的山岳好手,好些還是她以前的伙伴,挑戰K2峰,世界第二高峰。眼下只有一個問題——汪達拄著柺杖。一年前,她在攀登俄羅斯高加索群山時摔傷,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引起許多併發症。
連走路都不靈便,還得靠柺杖,多半人早就放棄攀登K2峰的打算。但是,汪達跟許多的波蘭登山家一樣,被訓練成外人難以想像的堅忍與果決。K2是汪達的夢想,她渴望好好端詳這座山,再怎麼樣也得撐到基地營。
臉色凝重,好勝心卻極其旺盛,汪達跛行一百五十公里,展開前往K2峰山腳的徒步旅程,想要追上其他隊員。柺杖謹慎的落在突出的懸崖邊,在窄窄的山徑上,勉力維持平衡。一小時復一小時。一日復一日。見到她的村民個個目瞪口呆——這個美得異常的小女子——靠著柺杖,一步一挨,徐徐穿過巴瑞都河谷。即便當地挑夫見識過她在先前遠征展現的毅力堅忍,依舊對她的勇氣敬畏不已,在岩石上刻下「不死汪達。汪達,萬歲!」
幾天之後,她抵達巴托羅冰河(Baltoro Galacier),路況更加惡化。小碎石跟較大的石礫讓位給岩錐(talus)。兩支登山杖備受道路摧殘,現已不堪使用,她又取出新的一對。汪達雙手滿是水泡的破皮,胳肢窩也磨到紅腫。
距離基地營只剩幾小時的路程,疲倦席捲而來;體力放盡的汪達,無力欣賞周邊壯闊的花崗岩牆絕景,癱倒在石塊上,按摩抽痛的雙腿,默默的啜泣起來。她的同胞登山家亞捷.庫庫奇卡跟克提卡.歐特克朝K2峰基地營前進之際見到的汪達,就是眼前這番狼狽的模樣。無堅不摧、熊一般強壯、人稱「朱瑞克」(Jurek) 的庫庫奇卡,實在看得不忍心,一把將她抱起,持續往前。瘦小卻結實的歐特克順手拾起汪達的登山杖。兩人輪流換班,硬是帶著汪達,走完剩下的路程。
說實話,朱瑞克並不太欣賞女性遠征隊這種點子,就算是他素來佩服汪達也一樣。
他覺得汪達太把登山當作一種競爭性的運動,才會堅持跟其他女性一起,藉機較量。他只想爬山。其他的男性隊員的想法也差不多。不過,汪達各方面的關係都很好,還設法取得K2峰的登山許可。只要能讓他跟歐特克一路尾隨,兩人倒也不會驕傲到拒絕參與。
歐特克跟汪達比較熟,由他開口去跟汪達商量,在這次登山活動中,兩人該扮演什麼角色。他們倆絕不擋道,他承諾,也不會採行同樣的登山路線。他知道,汪達非常堅持這次遠征必須全是女性登山家,至少要被外界認定沒有任何男性協助。他們只想讓巴基斯坦當局知道,他跟朱瑞克是隨隊的攝影師以及記者,協助這批女生在穆斯林國家跟當地人打交道。他深知汪達的願望,一定傾力尊重。
歐特克就是這種性格。其他登山家總是有話直說,他卻比較深沉,開口前,一字一句都會斟酌。他的觀察力讓人印象深刻,不只看得穿事實,態度、感受的細微變化,也都能了然於心。他是被稱為「沉思者」的登山家,出身教育跟文化背景都不差的家庭,對於好幾種語言都展現高度的好奇心。
三十出頭的克提卡.歐特克來自波蘭西部、原為德國領土的小村莊——斯克辛卡(Skrzynka),他在自然圍繞的環境裡度過早年歲月。十歲那年,他搬到飽受戰火蹂躪的華沙,童年就此陷入消沉。他在大學研讀電機,好像也提振不了什麼士氣;就在這個時候,他接觸到登山。他攀爬岩石的天分為他贏來「野獸」的稱號。他很快就發現登山是會上癮的;只是當時的他並不知道,這種癮頭對他來說是多麼危險的陷阱。
朱瑞克.庫庫奇卡比他這個認真緊張的朋友小一歲,體型魁梧雄壯;相較而言,歐特克比較像是緊緊纏繞的彈簧。朱瑞克沉默寡言。要說能引人注意的地方,大概就屬他的一雙眼睛,溫暖友善,還帶著一絲笑意。朱瑞克誕生於一九四八年,跟波蘭重要的登山高手一樣,都是主修電機,日後讓他得以進入煤礦工業任職。工作地點在卡托維茲,波蘭西南部的煤礦業重鎮。但是,他真正的職志卻是登山。十七歲那年,他接觸到攀岩,就此感受到無窮的驅動力,帶著他一步步攀向世界的最高峰。在群山峻嶺間,他履險如夷。
朱瑞克、歐特克、汪達:三個登山界的傳奇,此時,全都在巴基斯坦,奔向相同的目的地——挑戰世上公認最難征服的十四座絕頂,全都超過八千公尺,高度難以思議。
果決的意志與永不消磨的驅力,讓他們成為世上最受尊敬的三位登山家。但是,成就絕非意外,耀眼的地位全都起自貧賤。跟許多人一樣,暴亂的毀滅力量,塑造了他們的生命起點——誕生在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中,歷經兩個暴虐的外來政權的統治:德國與蘇聯。儘管汪達、朱瑞克與歐特克幸運逃過一劫,但是戰爭的殘酷卻鍛鍊出他們的堅忍與毅力。所有登山菁英背後的故事,相去不遠:歷史強化了他們的身體與心智。他們不單是登山家。他們是波蘭的登山家。
...
汪達呱呱墜地前四年,波蘭的命運已然底定。一九三九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天,納粹與蘇聯簽訂《莫洛托夫/李賓諾甫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也就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兩個國家在條約中宣稱,雙方不會兵戎相見,將以和平友好的態度處理所有「問題」。率先動念妥協的是德國,免得陷入兩面作戰的死局——這是他們不計任何代價都要避開的窘境,畢竟前一次世界大戰的殷鑑不遠。
所謂的「互不侵犯」本身就頗具反諷意味。德蘇簽下祕密協定瓜分波蘭與兩國之間的波羅的海區域;蘇聯用以做為緩衝區域,延遲來自西方的攻擊。日後的血腥鎮壓與恐怖統治,全是這個密約的後遺症。
協約簽訂不到兩週,納粹德國暗地籌畫,用一個陰狠巧妙的詭計,掀開兩手策略的底牌。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德國士兵偷襲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格利維采(Gliwice)德語廣播電臺。這次的攻擊行動是百分之百的騙局,其中至少有一個暴徒,根本不是德國士兵,而是一個定讞罪犯,因為同意參加這次行動而得到緩刑。任務完成之後,他被一個真正的德國黨衛軍(SS)擊斃。黨衛軍除去他被鮮血染紅的德軍制服,換上波蘭軍隊的制服,扔在現場交給波蘭警方處置。第二天,全世界都得知了這個震驚的新聞:波蘭竟然主動攻擊第三帝國。
在這起陰謀之後,德國對於波蘭的報復逐漸升級:空中攻勢、俯衝轟炸機、街頭炸彈與冷不防射來的步槍子彈。不到一週的時間,波蘭人就守不住邊界了;到了第二週結束前,華沙遭到包圍。波蘭寡不敵眾:納粹德國擁有兩千六百輛坦克,波蘭只有一百五十輛;德國戰機兩千架,波蘭四百架。波蘭人倒也不特別驚慌。他們知道只要擋下德國,撐足兩週,已經對德宣戰的西方盟軍,一定會發動重大攻勢,抒解他們壓力。
如意算盤完全落空。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號,大出乎波蘭與舉世意料之外,蘇軍突然越過波蘭的東部邊界。這正是德蘇密約中的老謀深算。波蘭政府撤離華沙,放任人民自行防衛。老百姓設法又維持十天。態勢已經很明顯,德蘇兩國根本就是勾結漁利,聯手瓜分波蘭。缺乏防禦掩護,波蘭軍隊無處可逃,共計六萬人陣亡,十四萬人負傷。聯軍始終不曾出現。絕難想像西方世界會為了波蘭,冒著開罪盟友蘇聯的風險。
德國與蘇聯公開分享戰利品。蘇聯占領東北面,第三帝國竊據波蘭西部,還立即施行軍法管制,指定新併吞的領地為「工作區塊」,膽敢反抗的人只有兩種下場:送進集中營或立即處死。
兩個國家痛恨波蘭人的程度,都不遜於對猶太人惡感。納粹的軍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忙得不可開交,頻繁往來波蘭與德國之間,分類、隔離波蘭人民,決定他們的最終命運。一個村落接著一個村落,每個人都被迫向納粹當局登記,根據不同的分類,發放不同的身分證、工作證,還有最重要的卡路里兌換券。「第一級」居民具有德國血統,每天能得到四千卡路里。波蘭工人日得九百卡路里。猶太人,基本上什麼都沒有。
軍隊把波蘭人從家裡趕出來,騰出空間給德國軍官居住。汪達的父親茲比格涅夫.布雷沙凱維茲(Zbigniew Błaszkiewicz)當時住在波蘭東南部的拉登(Radom),在兵器工廠擔任技工,被迫潛逃,免得鋃鐺入獄。士兵只給他幾小時,收拾可憐的家當,打包離開。當時他只想逃得越遠越好,索性搬到東北部的普倫蓋(Płungiany,稍後併入立陶宛)。隨後,他認識還娶了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當地婦女,瑪麗亞.派特昆(Maria Pietkun)。瑪麗亞的全副熱情,全都投注在翻譯埃及象形文字上。
幾乎從新婚開始,兩人之間的關係就陷入緊張。茲比格涅夫窮怕了,節儉度日,對於未來憂心忡忡,還在日記裡坦承,他其實有點蔑視這個我行我素的太太。在四個小孩中,汪達排行老二,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誕生在這個分裂的家庭、分裂的國度。
...
折磨波蘭的不僅僅是德國。在東北部,汪達的老家,蘇聯也把波蘭老百姓往集中營裡趕,把他們當作奴隸剝削。一九四○年到四一年,一列列的貨車迆邐向東,滿載著胡亂安上罪名的波蘭「罪犯」。他們成堆站在原本運牲口的車廂內,沒窗戶不說,車門還上鎖,一路不停,駛向幾千里開外。他們忍飢受凍,精神瀕臨崩潰,甚至被迫吃人肉。死在旅途上的人,就往車廂天窗外一扔。總數一百五十萬的波蘭人被迫離鄉背井,半數不曾生還。這個殘酷的數字,再次提醒世人波蘭慘遭瓜分的血淚史。
夾在納粹德國與蘇聯之間的波蘭,被有系統的矮化成奴隸國家;完全孤立無援,無力自衛。戰爭隨後轉向,德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攻擊蘇聯;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蘇聯竟然尋求波蘭人民的協助。這個構想完全不把波蘭當回事兒,但是,回應蘇聯的訴求,至少能拯救這個國家——但結果也只比免於滅種好一點,幾場大戰在波蘭展開,國土幾至糜爛。
儘管切割波蘭,蘇聯跟德國有志一同;但是,對於如何管理,德國卻有自己的盤算。根據他們的估計,約有兩千萬的波蘭人「極低度合適」「再德國化」,必須發配西伯利亞西部;大概有四百萬人因為具有德國血統,「適合」;其他的人乾脆悉數剷除。德軍沒收私人的土地、工廠與住處——自然是毫無賠償。對德國人來說,波蘭真是興建各種「營」的絕佳地點:「罪犯」營、流放營、政治犯與激進敵人營、勞工營以及系統性的種族滅絕營。盧布林(Lublin)、海烏姆諾(Chełmno)、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堡(Sobibór)、貝烏熱茨(Bełżec)與奧斯威辛(Auschwitz):這些地名永遠跟泯滅人性連在一起。只是屠殺計畫不只在集中營內推動。一九四○年到四三年,華沙猶太區居民就很有條理的被逐一殺戮,絕少疏漏。
一九三九年到四五年這六年的戰爭期間,超過六百萬的波蘭人失去性命——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其中只有百分之十死於直接的戰爭行動。剩下的,多半是波蘭的平民,慘遭處決,或者沒熬過飢饉與疾病,死於街頭與集中營。這些數字無助於外界瞭解他們歷經怎樣的苦楚,也無法讓人得知波蘭老百姓如何奮力求生,苦撐過那段歲月。
雖然外援斷絕,倖免於難的人始終在為祖國的獨立奮戰不懈。一九四四年,波蘭人民為了奪回首都,在華沙起義。這次行動一開頭就是烏雲罩頂,出師不利。第三帝國花了六十三天的時間,摧毀這個城市的歷史珍藏、醫院與橋梁。濫射更是家常便飯。十五萬華沙市民被殺,殘存的五十萬人被送進勞改營。城市清空之後,德國工程師進駐,燒掉、摧毀所有遺物,尤其鎖定歷史遺跡、教堂與檔案。德軍將希特勒的指令謹記在心。他說,華沙「應該夷為平地,不留痕跡」。
一九四五年初,蘇軍挺進華沙;沒花多久的時間,就把德軍趕跑,在這城市建立新的宗主政權——共產黨。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和平」終於宣告降臨,全波蘭納入蘇聯的統治,掙脫德國,得到「解放」——僅僅是美其名,現實生活跟這兩個字完全沾不上邊。新來的蘇聯老闆,縱橫捭闔,完成好幾筆高階買賣,肆意劃分邊界。汪達誕生的普倫蓋,如今劃歸立陶宛,改名為普倫吉(Plungė)。熬過六年恐怖統治與殺戮,僥倖撿回一命的波蘭人茫然無語。走在路上不怕遭到冷槍射殺的日子,已成遙遠的過去,不復記憶。社會結構全面被抹殺,沒有知識分子,自然也沒有任何猶太人。倖存者每過一天,他們曾經熟知的波蘭面貌,就跟著模糊一分。
...
歷經大戰的波蘭殘破不堪,卡托維茲周邊以及波蘭西南部更是受損嚴重,格外慘不忍賭。這裡就是亞捷.庫庫奇卡的老家。戰後,此地力推一九五○年公布的六年經濟計畫,面貌為之大變。最受計畫青睞的,絕無疑問,就是重工業——無限追求鋼鐵產量。卡托維茲位於重工業區的核心,蘇聯特地建鐵路連結卡托維茲與邊界,運送此地鋼鐵廠數量巨大的生產品。波蘭的登山骨幹,也在這個工業重鎮崛起,多半是在鋼鐵廠任職。
儘管經濟掛帥,波蘭人民卻是一片意興闌珊。薪資固定,無論你是做多——還是做少。雖說無力對抗體制,消極怠工還是做得到的;而這也讓波蘭的經濟成長陷入停頓。底層偷雞摸狗,做事有一搭沒一搭,生產力低迷、品管鬆散、效率不彰。人們寧可省下力氣去兼差,或者站在長長的人龍中買麵包。回想起他們已經忍了這麼多年,怒氣更是不打一處來:抗德戰爭、抗蘇戰爭、夾在德蘇大戰間,國土淪為戰場、蘇聯統治,再次瓜分。波蘭人壓根瞧不起仗著蘇聯撐腰,統治他們的傀儡政權,更在意自己能不能好好活下去。
在艱苦度日的氣氛中,汪達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她面前展開——一個遠離灰暗、污穢街道的大自然,裡面有岩石、友情,還有自由的感受。她的攀登遠征很快的就離開鄰近懸崖,開始挑戰卡托維茲西北部、以石灰岩為主的侏羅群山(Jura Mountains)、接近東德邊界的沙岩懸崖,最後來到捷克邊界的高塔特拉山(High Tatras)。崇山峻嶺成為她獲得自由的綠洲。就跟她念書的態度一樣,汪達的登山進程,也是很有系統的,認定目標,便堅持到底。她的妹妹後來說:「對她來說,登山就跟藥物的作用一樣。根本不用費什麼心思,自動進入血液,被她完全吸收。」她的自信心越來越強,也越來越好看。充滿陽剛氣的登山隊裡,她是罕見的女生,幾乎每個男生都被她燦爛的笑容迷得神魂顛倒。
...
一九六四年,二十一歲的汪達,從大學畢業的同時,開始挑戰阿爾卑斯山。不巧的是,她偏偏手臂囊腫感染,幾乎無法登山。但卻因此認識了一個生性體貼的醫師——賀默特.夏斐特(Helmut Scharfetter),來自因斯布魯克(Innsbruck),不但治好她的感染,還安排她上一堂登山急救課程,抒解她的失望。之後,他還陪著她攀登齊勒塔爾阿爾卑斯(Zillertal Alps)。他對她的第一印象是:服裝配備儘管破舊,但這個聰明的女孩吸引力實在無法抵擋。這個好醫生最終在她的生命裡,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她返回弗次瓦夫之後沒多久,電話鈴聲響了。一個民防部門的人打電話給她,邀請她到弗次瓦夫最高級的咖啡廳,喝點飲料。汪達同意了,在指定時間前往赴會。兩個穿著制服的人歡迎她,正式自我介紹,出示證明文件,請她落座。他們點了又濃又香的咖啡,還很大方的切了好幾塊蘋果蛋糕。
高的那個露出淺淺的微笑,大力稱讚汪達:「妳是登山家——在波蘭登山界赫赫有名。」
「是啊,我是爬過幾座山。也許小有名氣,但稱不上赫赫有名。」她回答,有點憂心。
矮的那個,臉色蒼白,在狼吞虎嚥蛋糕的空檔插嘴說:「爬山很辛苦,又危險。」他又咕嚕一口,「妳的身體一定很好吧,經常旅行?」
「是啊,為了登山只好旅行。非常走動不可,如果我想成為一個真正的登山家的話。」
他們兩個人的身子都往前傾,眼神變得更加集中,端詳汪達。「妳最近去過奧地利。感覺如何?妳一定碰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吧?」
汪達往後一靠,離兩個人盡量遠點。「當然,我遇見很多很有趣的人。登山家,當然。」
「妳算是有點特權的女性。經常出國旅行,認識很多外國人。這樣的日子,妳應該很想繼續過下去吧?」
汪達終於弄明白這一連串的問題所為何來:他們希望她能跟祕密警察合作!他們還想繼續說服,汪達卻已經勃然大怒。最終她實在按捺不住,朝著桌子狠狠一搥,「你們到底是想要幹什麼?要我幫波蘭當間諜?這太卑鄙了,你們是侮辱人嗎?怎麼可以叫我幹這種事情?」
吸收細胞是常用的手法。蘇聯打造的監視機器,倚靠汪達或者她的登山伙伴充任「志願者」——因為他們經常離開波蘭,在海外旅行。
鄰近桌子的客人伸長脖子看著汪達,她的眼睛噴出憤怒火焰,高聲喝叱,夾雜著憤怒的手勢。那兩個人鬼鬼祟祟的打量周遭群眾的反應,趕緊跟汪達保證這不過是閒談,犯不著這樣大題小作,一邊安撫她,一邊找來侍者結帳,趕緊護送汪達離開咖啡館。一走出門,兩人態度一變,警告她若膽敢把這次會面跟談話內容告訴別人,她這輩子就沒機會再攀登阿爾卑斯山了——離開波蘭更是想都別想。
從此之後,就沒有特務想要吸收她了;但是,其他登山家未必。好些人日後透露,他們每次海外登山返國之後,都被要求立刻回報;如果他們想要取回護照,進行下一次的國際登山遠征,就得被迫跟當局「合作」。
特務對他們特別感興趣,基於下面幾個原因。登山家經常出國,在海外旅行、一待就是好長的時間,當局認為,他們正是「西方資本主義毒苗滋生的溫床」。更糟的是:他們還會把餘毒帶回波蘭,所以必須要監視——不得鬆懈。但他們同時也是最好的西方觀察者,把有價值的資訊,無論是政治、經濟或者生活方式,帶給當局做為參考。更重要的是:登山家很容易打交道,因為他們所得豐厚——旅行的自由;不合作,損失也慘重——只能窩在波蘭。登山家因此成為最容易下手的目標。每個登山社團的負責人都經常跟特務回報;外界也知道登山俱樂部裡面有很多線民。有的人會公開談論這種情況,有的絕口不提。某些登山家在跟特務密會之後,可以成功離境;有的卻被駁回。其中道理始終沒人說得清楚。在登山界越是有名望、越是經常出國的人,越不可能逃脫他們的控制。
延伸內容
【導讀】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
波蘭的,也是台灣的
◎文/詹偉雄(meters山岳文學書系總策畫)
Englishmen were waking up to the fact that “mountaineering” is a pastime that combines many advantages, and is worth pursuing as an end in itself, without any regard to any thought of the advancement of natural science.
英國人正逐漸領悟一個事實:登山,是擁有許多益處的一種消遣,因此值得將它當成最終目的來追求,不必再管它與自然科學進展的關係。
——威廉.A.B.柯立基(William Augustus Brevoort Coolidge),《The Alps in nature and history》,一九○八
Where does Mont Blanc end, and where do I begin? That is the question, which no metaphysician has hitherto succeeded in answering. But at least the connection is close and intimate.
白朗峰在何地結束?我,又要由從何處開始?這是問題所在,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位形上學家能成功回答。但至少,兩者的關係非常接近,而且親密。
——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The Playground of Europe》,一八七一
Each climber loses one finger or toe once in a while. This is a small but important reason for Polish climbers success. Western climbers haven't lost as many fingers or toes.
每一位登山者,偶爾都會失掉一根手指或腳趾,這正是波蘭登山家能取勝的一個微小卻關鍵的原因——西方登山者沒像我們失掉一樣多的手指或腳趾。
——汪達.盧凱維茲(Wanda Rutkiewicz)
Thanks to the mountains, I felt the taste of life. And not only there on high peaks, but also elsewhere: at home, at work, in the hardships and troubles of everyday life.
感謝山,讓我嚐到生命的滋味;不只在高聳的尖頂上,也在各處:在家裡,在工作中,在每天生活的艱難與麻煩中。
——亞捷.庫庫奇卡(Jerzy Kukuczka),《Ostatnia ściana》,頁一二四
Mountaineering is a complex and unique way of life, interweaving elements of sport, art and mysticism.
登山是一種複雜又獨特的生活方式,交織著運動、藝術與神秘主義等各種元素。
——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The Polish Syndrome〉,《Great Climbs: A Celebration of World Mountaineering》,頁一九八
這本書對作者伯娜黛.麥當勞女士來說,是一本生命轉捩點的書。她從小到大成長在加拿大北方廣袤的大草原,不見群山,音樂是她的本職學能。上世紀九○年代因緣際會,進入加拿大洛磯山脈的邦夫文化中心擔任主任,主辦山岳文化祭,在那裡,她接觸到來自全世界的登山家,被那些高張力的生命故事所吸引,二○○六年她決定辭職,矢志要用她的餘生,將這些故事寫出來。《攀向自由》並非她寫作生涯的第一本書,但卻是她第一本接近完美結構的非虛構類創作,二○一二年出版後幾乎囊括全球所有山岳或自然文學類的大獎,在她的筆下,許多生命謳歌出最讓人心碎的樂章,過目遲遲不忘。
這本書對於導讀者我而言,也是一本扭轉視野的力作,謙遜地說:是這本書觸動了我選輯「meters山岳文學經典」的一絲絲抒情雄心。在這本書裡,對一位「沙發登山家」([Armchair Mountaineer〕英語世界對山岳故事讀者的暱稱)來說,他不僅可在一定的高度上,睥睨喜馬拉雅和喀喇崑崙山間豪邁、酷冷的風光,見識地球大爆炸後原始、粗礪的岩石冰霜表面,還可進入主角人物的肉體磨難和哲學世界,讀者一方面遭遇最華麗、璀璨的探險,目不轉睛,又必須直面二話不說的墜落死亡或雪崩消殞,無限創傷;你在沙發上不禁抬頭凝望,要咀嚼這難忍片刻,卻又發現世界與時代的各種力量糾葛,吵吵鬧鬧地構成這些故事的偌大背景:聽到團結工聯在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巨大噪音,聽到瑪麗安.菲斯佛(Marianne Faithfull)憤怒與不安的歌曲(波蘭登山家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說:她就像波蘭的歷史,所有人都進來,所有人都創造巨大破壞),聽到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的低語呢喃(在攀登有「閃耀之壁」稱號的加舒爾布魯四號峰[Gasherbrum IV〕時,克提卡聽到舞動的繩索唱出了史翠珊的歌聲)……。
但在身為讀者的你好整以暇地跌入沙發之際,且容我來嘮叨一些瑣碎、但不無章法的一些歷史小事,它們有助於我們鞏固閱讀山岳文學的信念,明白人類在與山遭遇時,那莫名的高亢感受其實其來有自。登山既是一種體能的運動,也是一種自我確證的過程,它們往復在登山家的身心之間,創造了一種非常寬宏的自由體驗,這正是十九世紀中葉起登山家們蜂擁尋山、上山、殉山的義理所在。而上世紀一九八○年代的波蘭登山家們,以優雅剛毅的搏戰,幾近完美地體現了這個過程,這篇導讀有責任提醒讀者注意這件事。
有紀錄的現代登山活動,開始於法國大革命前的一七八六年,法蘭西東南角夏慕尼(Chalmonix)地方的一位採礦工賈克.巴馬(Jacques Balmat),和他的醫生朋友賈布耶.派卡(Gabriel Paccard)聯袂登上了白朗峰(Mont Blanc,海拔四八○八公尺,阿爾卑斯山脈最高峰)。這個隨性而起的壯舉,透過當時歐陸傳媒的散布,讓兩人獲得一筆意外的財富,吸引不少的歐陸人接踵啟後。
但是,放眼兩世紀多前的當年歷史,沒有英國人參與的事,怎能熱絡得起來?巴馬與派卡登頂之後,平均每年只有一組人馬走上白朗峰,直到一八五○的世紀中葉。
當時,維多利亞女皇即位沒有多久,兩位英國人來到阿爾卑斯山,他們登頂後回到英國,各自出版了遊記,一下子掀起了登山的狂風巨浪。數以千計的英國人乘著橫越英吉利海峽的蒸氣渡輪,接上法國國家鐵路的燃煤火車,一下子便來瑞士和法國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山腳下,開啟了人類登山史上第一個黃金年代。
這兩個英國年輕人都具有典型的現代氣質,熱衷於身體運動,鉅細靡遺地記錄生命經驗,而且善於自我宣傳。其中的一個名叫艾伯.史密斯(Albert Smith),他在一八五一年登上了白朗峰,回國後出版遊記,並在倫敦皮卡迪里圓環埃及劇院策畫〈白朗峰攀登記〉現場秀,於一八五二~八年間演出了兩千場,盛況空前。另一個叫做艾佛列.威爾斯(Alfred Wills),他於一八五四年登上位於瑞士觀光小鎮格林華德(Grindelwald)頂上的韋特洪峰(Wetterhorn,海拔三六九二公尺),並於兩年後出版《漫步阿爾卑斯高山》(Wanderings Among the High Alps),一下子就成為暢銷書。
在史密斯攀登白朗峰前,歐洲人並不熱衷於她,半個多世紀登頂紀錄只有四十次,但待得史密斯號召的英國人湧入,五年內的攀登次數就來到八十八次;在史密斯之前,阿爾卑斯山前二十五座高峰中,只有五座被人類足跡踏上,而且都是歐陸人,史密斯之後三十年間,所有高峰全都留下了人類的印記,而二十座處女峰的首攀中,就有十七座來自英國人。
相較史密斯魅惑人心的現場敘事和華麗壁畫,威爾斯的貢獻則比較幽微,他是第一個揭櫫「運動動機」為唯一爬山真理的登山作家,他的書鼓吹為登山而登山,與彼時的當代大儒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所倡議的折衷浪漫主義理念——山是透過一定距離外的視覺欣賞來沉澱出心中真理的,而不是用來攀爬的——針鋒相對,但卻意外地受到登山社群的熱烈擁抱。人們相信:近距離——透過身體的直接接觸——體驗山,登山家得以獲得一種對外在自然的獨到貼身知識,這種被後來登山家與文化評論家馬丁.康威爵士(Sir. Martin Conway)稱之為「冰冷石頭似的實在」(cold stoney reality)的切身感,成為晚期維多利亞登山家們爭相自我砥礪與訓練的目標,更遠地啟迪了後世登山者對遙遠八千公尺巨峰的嚮往——為了要讓身體獲得更新、更強的體驗,登山家勢必得尋找更偉大的自然,置身於更嚴峻的危險之中。
英國當代山岳文化史研究者艾倫.麥克尼(Alan McNee)指稱這群維多利亞世代的登山者為「新登山家」(New Mountaineer)。從外表看來,他們身體強健、精神大膽、具有足夠攀登技術,登山過程有組織而且系統化,他們涵泳許多新的知識學門,也陶醉在運動的競技中,熱衷於現代性的各種理念,不覺得使用最新的裝備與技術來幫助他登上峰頂,有任何違和之處。從內在的情感層面看,他們非常注重身體與山岳地景直接接觸所產生的直接感受,麥克尼稱之為一種「觸感的崇高」(haptic sublime),以與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一七五七年撰寫《對崇高與美麗意念起源的哲學探究》時所指稱的「情感的崇高」有別。
一八三七年即位的維多利亞女皇,在位長達六十三年,任內經歷了英國與歐洲在科技、人文思潮與社會的重大變遷,「維多利亞時代」幾乎等同於「現代化」的代名詞,「新登山家」的誕生,隱約與那個時代中新興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有關:更關心審美顫慄(aesthetic sensation)經驗中的身體經驗,而非精神想像;對成就與倦怠的生理學產生新興趣,當然也吸吮著各種招牌式的「維多利亞式驅力」(Victorian drive):熱衷社會地位的競逐、規則的條文化與系統化、對萬事萬物進行分類。或許是由於感覺多元豐富,許多「新登山家」都在攀登生涯中成為作家,其中最負盛名的當數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的父親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他所寫的《歐洲的遊樂場》(The Playground of Europe),一八七一年出版,被視為是山岳體驗文學的第一本經典。此外,艾伯特.馬默里(Albert F. Mummery)身手矯捷,完成了不少阿爾卑斯山未登峰的首登,他的《我在阿爾卑斯與高加索山區的攀登》於一八九五年出版,也是世紀之交人人爭相一睹的暢銷書。
全世界有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巨峰,它們羅列在中國、尼泊爾、巴基斯坦的邊境或南北境內,主要屬於喜馬拉雅山脈,在遙遠的西端,造山運動出現了劇烈的糾結而脫離了喜馬拉雅軸線,當地人稱之為喀喇崑崙(Karakoram,突厥語「黑色礫石」之意),十四座中的四座,便踞居在這道寂寞邊境最荒遠的地帶。
這十四座大山,在這本書中將反覆出現,為了熟悉與方便,先在這裡,依序列出它們的名字與高度:1. 聖母峰(埃佛勒斯峰,八八四九公尺) 2. K2(八六一一公尺) 3. 干城章嘉(八五八六公尺) 4. 洛子(八五一六公尺) 5. 馬卡魯(八四八五公尺) 6. 卓奧友(八一八八公尺) 7. 道拉吉里(八一六七公尺) 8. 馬納斯盧(八一六三公尺) 9. 南迦帕爾巴特(八一二六公尺) 10. 安娜普納(八○九一公尺) 11. 加舒爾布魯一號(又稱「隱峰」,八○八○公尺) 12. 布羅德(八○五一公尺) 13. 加舒爾布魯二號(八○三五公尺) 14.希夏邦馬(八○二七公尺)。
就地理位置而言,干城章嘉最東,南迦帕爾巴特最西,簇擁在喀喇崑崙山區的K2、加舒爾布魯一號、布羅德與加舒爾布魯二號最北。就發現時間論,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英國殖民官員認為干城章嘉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岳,然而在一八四九年大三角測量隊的最新發現後,聖母峰成為第一高峰,一八五六年,另一支由蒙哥馬利中校率領的測量隊發現了K2,干城章嘉退居第三。
十九世紀末,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及遠航世界的想像,在阿爾卑斯山區建立起信心和熱忱的「新登山家」們,開始將眼光望向亞洲,第一個來到八千公尺巨峰山下的,便是英國登山家馬默里,他才情洋溢,身手與智慧過人,除了剛出版的著作成為倫敦暢銷書,他綜合豐富經驗而發明的輕量高山帳篷,被視為是劃時代的現代登山裝備。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與兩位挑伕在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爾巴特峰北面的拉奇歐特山壁(Rakhiot Face)探勘時,一場雪崩襲來,他們瞬間被吞沒,年方四十的馬默里是這座大山的第一位喪命者,截至一九五三年奧地利登山家赫曼.布勒(Herman Buhl)首次登上絕頂前,總計有三十一位登山家喪命於追峰道途之中。
從十九世紀初英國人因為休閒和娛樂而登山,到世紀中因為科學理解走上技術攀登,以迄世紀末馬默里因為追求巔峰經驗而殉山,登山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有了重大轉變,在他那本堪稱經典的《我在阿爾卑斯與高加索山區的攀登》最後一章,名為〈登山的快感與懲罰〉(The Pleasures and penalties of Mountaineering),他這麼說:
「真正的登山家是一個浪遊者,說他浪遊,不是指他在山間旅行,來來去去,走在前人開出的確鑿步道,像自行車手沿著英國收費公路騎乘這樣,我指的是一種人,他只喜歡去那些沒有其他先人到過的地方,當他抓緊某些岩塊時,他因這些石頭未曾碰過其他人類的指尖而愉快;他踽踽獨行爬上冰雪遮覆的岩溝,與眼前的濃霧和雪崩相比,自己灰暗的身影頓時神聖起來,因為這是『地球大爆炸』來萬物所見的第一人。
換句話說,真正的登山家是嘗試新攀登紀錄的人,相對地,不論他成功或失敗,他都在拚博的趣味與歡樂中獲得愉悅。那些讓人筋疲力竭的赤裸岩塊、山脊上方正陡峭的岩階,以及岩溝裡浮凸而起的黑色積雪,正是他生命呼吸的要義。我不必假裝能去解析這樣的感覺,也更難去讓不信者明白,只有透過感受才能理解登山,它帶來巨大的快樂,讓血脈賁張,摧毀著犬儒主義的每一道蹤跡,也重擊著悲觀主義哲學的根柢。」
馬默里在喜馬拉雅山上的消殞,使登山界明白八千公尺大山是完全和阿爾卑斯山不同的怪物,必須要用國家級的力量來對待,從二十世紀以降,有三個國家分別對三座大山發起史詩般的遠征,期望這些倔傲的山巔,能臣服在帝國的科技、兵力與財貨權勢之下:英國隊因其對印度殖民的地緣政治,優先選擇了聖母峰(著名的喬治.馬洛里參與了三次),美國隊瞄準喀喇崑崙山區的K2,德國隊則針對南迦帕爾巴特。說來弔詭,這些國家在半世紀內屢敗屢戰,但第一個登上八千公尺峰頂的卻是法國隊,他們在尼泊爾開放外國登山申請的第一年(一九五○),申請到了攀登道拉吉里和安娜普納峰的許可,最終在六月三日那天,由領隊莫伊斯.荷佐(Maurice Herzog)與他的法國同袍路易.拉荷那兒(Louis Lachenal)登上八○三九公尺的山巔,這是人類第一次超越八千障礙,而且是他們第一次攀登就完成目標,但還是付出了慘痛代價:路易的腳趾嚴重凍傷,全部切除,而莫伊斯則是腳趾和手指都必須截肢。
接下來的故事,便是二十世紀登山史的主要章節了:英國隊在一九五三年成功地由艾德蒙.希拉瑞爵士與雪巴人丹增.諾蓋登頂聖母峰,完成英國史上最壯烈探險篇章的最後一筆;一個月之後,奧地利人赫曼.布勒登上南迦帕爾巴特峰,一償德語系山客的夙願;一年後,義大利隊攻克了K2的冰雪防線。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山陸續站上了各路國家遠征隊的腳印。這些動用龐大資源,在偏遠的山區動輒雇用超過一千名挑伕,在冰雪山徑上布滿高地帳篷,隊員彼此接力扶持,與雪巴輪流運補輜重物資,架設固定繩索,務求最後一刻靠著最強隊員登頂,榮耀整個國家共同體的企圖心,仍是延續著上世紀末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攻城掠地的遺緒。在這種功利主義的攻頂競賽裡,維多利亞時期萌芽起來的「新登山家」逐漸隱藏進時代的暗角,一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波蘭登山隊橫空出世似地進入全新的「喜馬拉雅難題」之中,一群頂著「受苦的藝術家」(the artist of suffering)冠冕的波蘭人刷新八千公尺登山的新紀錄,才再度把「新登山家」的內在哲學與信念,帶上風雲舞台的中心。
所謂的「喜馬拉雅難題」乃是:如果全世界最高的十四座山峰都踏上了人類的足跡,那麼還有哪些挑戰,留待有抱負的登山家來攻克?當時西方登山社群的答案是:八千巨峰的新路線、垂直大岩壁以及冬季攀登。波蘭國家隊選擇「冬季攀登」做為加入英美法義登山強權行列的敲門磚,而其中的更強者,同時也在「新路線」與「大岩壁攀登」兩項課題中大放異彩。
冬季高海拔地區的厚雪、強風、低溫,不僅需要更強的體能、絕佳的技巧,還需要一種「受苦的藝術」,譬如能在攝氏零下四十度的雪坡中露宿、忍受三天以上斷糧或缺水的身心煎熬,在幻聽、幻視、缺乏睡眠的迷離情境中仍能挺進。波蘭人在自家國度的塔特拉山群(Tatras)的冬天裡,練就了他們對抗酷寒的本事,塔特拉的海拔雖然不高,但它的地形卻十分破碎,岩場上雪不多,但卻被裂縫割裂,登山者必須脫掉手套,赤手來爬,波蘭黃金年代的大家長安德烈.扎瓦達(Andrzej Zawada)就說:「告訴我你冬天在塔特拉爬了哪些路線,我就可跟你說你到底是強還是不強!」
一九八○年二月十七日,克里茨多夫.維利斯基(Krzysztof Wielicki)與列社克.奇希(Leszek Cichy)爬上迷茫的聖母峰頂,完成人類史上第一次八千公尺(而且還是世界第一高峰)的冬季攀登,而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波蘭人陸續完成了另外七次巨峰的首次冬攀,英國登山媒體震驚不已,以「冰峰戰士」(Ice Warriors)的稱號,來讚譽這群名字唸起來非常拗口的怪客。除此之外,波蘭人還在八千公尺之上開闢了二十四條新路線(第二位的日本開拓了十五條,而英國僅有八條),完成了十三座七千公尺未登峰的首登,這段時期號稱波蘭登山的黃金年代,他們總計發起了四十趟七千公尺以上的遠征,成功率達到七十五%,不僅填補了波蘭在世界登山史中的空白,而且改寫了「新登山家」可在荒涼山岳中拚搏求生的可能性。只是這樣的代價也非常高昂,這十年間有三十一位登山家喪命,包括獲首位完成十四座八千巨峰攀登的義大利登山家萊恩霍爾德.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稱讚為「世界最偉大」的奇才亞捷.庫庫奇卡(Jerzy Kukuczka)。
庫庫奇卡是繼梅斯納爾之後第二位完成十四座大滿貫的登山家,波蘭登山社群形容他是「一頭友善、沉默的熊」、「光靠喜馬拉雅石頭即可維生的男人」,大滿貫路上他只花了梅斯納爾不到一半的時間(七年十一月十四天),而且其中十座是新路線,還包含四次冬攀,難度無與倫比。一九八六年夏天他從K2南壁登頂的新路線,征服許多出挑的雪簷和垂直崩壁,克服多夜露宿,在落石和雪崩間匍匐,被稱為形同自殺式的攀登,這條路線迄今無人走上第二次,號稱「Polish Line」。完成十四座後,庫庫奇卡耿耿於懷於第一座爬上的洛子峰走的是傳統路線,因此想方設法要從它艱困的南壁(由基地營到峰頂,垂直高度三千三百米)開出一條新路線,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八千兩百公尺的岩壁上踩空,一根從加德滿都舊貨市場買來的七米釐繩索撐不住重量而斷裂,他的確保繩伴眼睜睜看著庫庫奇卡直線墜落兩千米下的冰河。他的死訊同時也敲響了波蘭黃金年代的輓鐘——柏林圍牆倒塌,華沙公約解散,波蘭開始民主化,除了登山家折損凋零,孕育受苦藝術家們、克提卡比喻為「鐵鎚與砧板夾擊」的苦難社會主義體制也解組了,雖然無盡荒謬,但世事確實如此:「困頓造就舉世一流的登山家,繁榮卻使人瞻前顧後」(頁四九八)。
《攀向自由》主要環繞著三位超級巨星的主角而寫,除了幾近無堅不摧的庫庫奇卡,還包含第一位登上聖母峰與K2的歐洲女性汪達.盧凱維茲(Wanda Rutkiewicz),以及二○一六年世界金冰斧終身成就獎得主歐特克.克提卡,他們個性迥異,被不同的身世推向山岳巔峰,卻又在不同生命階段彼此交織,開張起波蘭登山界斑斕多彩、飽含伏特加滋味的生命圖譜,是作者寫作功力所在。
盧凱維茲於一九九二年命喪於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頂之下,她婉拒了隨行同伴的下撤懇求,一步步走向吞噬她的狂風暴雪。她的一生充滿悲劇與死亡,但絕大多數人卻只知道她的香水、迷你裙和謎語一樣的鬢影,比她小三歲的克提卡卻活了下來,他說他生性膽小、多疑,而且有一種反社會的傾向,因此在庫庫奇卡與梅斯納爾的摘峰競賽中急流勇退,他也不像盧凱維茲一樣急於證明自己,得以有餘裕挑選自己喜愛的路線去攀爬,創造出許多高強度攀岩的首登紀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克提卡和夥伴奧地利人羅伯特.蕭爾(Robert Schauer)出發,攀登有「閃耀之壁」(Shinning Wall)稱號的加舒爾布魯四號峰(Gasherbrum IV,簡稱G4)西壁,四號峰海拔七九二五公尺,排名世界第十七,在總計十座的加舒爾布魯群峰(當地巴爾提語:rgasha為「美麗」之意,而brum為「山」)中雖非最高,但它面向巴托羅冰河的西壁,是一道直挺挺向天際的二千五百米高大岩壁,任何由冰河西端跋涉過來的登山客,在準備叩關K2、G1、G2與布羅德四座八千巨峰前,都會看到它在夕陽中發散著光芒。原本克提卡的夥伴是庫庫奇卡,此前四年,他們曾是世界最強的高海拔登山二人組,完成過G1與G2的新路線首登,以及不可思議的布羅德北峰、中峰與主峰十公里縱走,但因為G4高度不及八千,庫庫奇卡急於搶攻其他八千大山而分道揚鑣。
美國《攀登》(Climbing)雜誌總編輯麥可.甘迺迪(Michael Kennedy)讚譽克提卡和蕭爾的攀登,是二十世紀登山史上最耀眼的成就,他們只帶了四天的食物和燃料,五天的飲水,打算用輕量化阿爾卑斯登山法速戰速決,沒想到攀岩過程非常艱辛,光滑的岩壁幾乎沒法插入岩楔,繩距由一般的四十米開到八十米,待得登上北山脊的頂點,離峰頂垂直高差不過二十五米,距離不及兩百米之處,他們又接連遇上好幾天暴風雪,挖雪洞避難三天。彈盡援絕之餘,兩人都覺得死線已過,只好從北山脊的路線撤退,前往七千一百米先前做高度適應時預藏的備援工具包處,在第九天取得飲水和食物,「這杯茶多麼濕潤!這三十顆糖多麼甜美啊!」克提卡在他的攀登報告〈加舒爾布魯四號峰的閃耀之牆〉中如斯描述。最後,預定五天的行程用了十一天,在冰雪中露宿十晚,卻沒有完成攻頂任務,但這趟行程中所動用到的技術、決斷、處置以及對惡劣天候的耐受力,都寫下了上世紀英國登山家所景仰的極限紀錄,足以讓後世人對「觸覺的崇高」這種身體化知識,留下深刻印象,克提卡如此說道:
「非比尋常的緊張和最麻煩之處,是身體在面對岩石、積雪和雲霧時,產生一種驚訝的屈伸調適能力,不可思議地突破難關。這些景象,至今仍歷歷在目,它們似乎被一種潛藏的、神祕的精神所創造。誰創造了你,如此可愛又靜謐的身形?」
《攀向自由》中所描繪的「自由」有多樣含義,一種說的是英國政治哲學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所謂的當代兩種自由:完全實踐自我意志的「積極自由」,以及得以掙脫外力宰制的「消極自由」。波蘭登山家在高壓的鐵幕生活中發現了高山是一片自由呼吸的空間,不僅舒緩了壓力,還在走私生意中積累財富,克提卡曾形容說他的生活一邊是惡魔(monster)而另一邊則是德布西(Debussy),這是「消極自由」戲劇性的體現。另一種自由,是法國現象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身體現象學》巨作中所說的「體感自由」,簡易地說:人在環境中,看似自由,其實並不自由,環境限制了人的行動能力,而人的身體無能跨越障礙,也造成了人的受限感,然而,一旦人類開啟了他的身體知識,在自然中領悟了穿越障礙的心法和魔術,他的受限感迎刃而解,這是一種本體論上的存有自由。在這個概念裡,崇山峻嶺的大自然,既是可以致人與死的天險障礙,又是讓人領略自由的靈魂伴侶,它複雜、它深邃,惟有這本書裡波蘭登山家的故事,能把它說得清楚。
現代生活中,我們被各式各樣的限制綑綁,從維多利亞時期、兩次世界大戰、東西冷戰、全球化到網路連結彼此的後孤寂年代,人們不得不捲入各種共同體的紐帶,放棄成為他自己。但是,有一群「新登山者」,他們在山與人對峙、消融、和解的關係中,發現了自由的可能,為此,他們拚死以赴,果敢、大膽、無畏。希望這本書是一只披頭四老歌中所說的飛翔黑鳥,引領台灣讀者產生對於自身生命的——一絲絲抒情雄心:「黑鳥在夜深人靜時吟唱,帶著這些沉默的眼神向前看,你的一生,你只等待此刻,此刻獲得自由!」
是的,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我們都置身於歷史中。編輯推薦
世人從未知曉,波蘭登山者們的苦難、孤高與榮光
文/謝至平(臉譜出版副總編輯)
談到波蘭,大家會想到什麼?或許會想起的是二戰 時,他們經歷納粹種族 清洗、又慘遭德蘇瓜分的血淚史;又或者會想到波蘭戰後被蘇聯吸收,成為共產主義 的附庸國,至九〇年代前的政經局勢長期委靡不振。但大家或許不知道,就在波蘭國內民不聊生的七〇、八〇年代,其實有群波蘭登山家不斷在世界的高峰上、尤其是聖母峰所在的喜馬拉雅山區,連連創下驚人紀錄,被國際登山界譽為「冰峰戰士」。究竟在物資極度缺乏、政治高壓箝制的狀況下,他們是怎麼辦到的?支撐他們的意志與動機又從何而來?
世界知名的加拿大山岳文學 作家柏娜黛.麥當勞 ,在任職於國際山岳文化重鎮「班夫文化中心」時,因緣際會與一群在那段黃金年代有過輝煌歷史的登山家們結識,不只從他們口中聽聞往日的榮光,更得知他們眾多已逝山友的生命篇章,充滿傳奇而動人,包含她曾有過一面之緣、第一位登上聖母峰的歐洲女性汪達.盧凱維茲、世界上第二個挑戰十四座八千公尺巨峰成功的亞捷.庫庫奇卡,以及受到舉世登山家尊敬的「登山界的思想家」歐特克.克提卡。
但即便波蘭登山家們有過這樣的輝煌創舉,卻在波蘭民主化、經濟崛起後逐漸受人淡忘,榮光不再,這段時期的故事也從未被完整講述。有鑑於此,柏娜黛.麥當勞花了數年時間,親身採訪仍在世的登山家與遺族們,並進行了大量的資料翻譯與蒐集,終於將這段寶貴而精采紛呈的歷史寫成《攀向自由 》這本書,完整重現於世人眼前。
本書出版後橫掃全球山岳、自然文學大獎,更獲頒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透過本書,我們不只將走進這群波蘭登山家們的生命與那個大時代,在疫情未歇之際,這部作品也能帶我們成為「沙發上的登山家」,以文字攀上高峰,體會波蘭登山家們於頂峰上尋得的無邊自由。更多編輯推薦收錄在城邦讀饗報,立即訂閱!GO
作者資料
柏娜黛.麥當勞(Bernadette McDonald)
知名加拿大山岳文學作家,亦為登山家、電影製作人、策展人。她是班夫藝術與文化中心創始副總裁,班夫山岳影展總監,也是班夫山岳書展的創辦總監。她的著作豐富,包括:《繩索兄弟:查爾斯.休士頓傳》(Brotherhood of the Rope:The Biography of Charles Houston)、《我在加德滿都打電話給你:伊莉莎白.賀蕾的故事》(I’ll Call You in Katmandu: The Elizabeth Hawley Story)等,亦贏得無數獎項,包括義大利的伊塔斯山岳寫作獎(ITAS Prize for Mountain Writing)、印度的刻苦.奈洛基山岳文學獎(Kekoo Naoroji Award for Mountain Literature);也曾獲頒班夫中心榮譽獎章、山岳文化與環境領域的亞伯他國王國際領導獎(King Alber Award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與金禧勳章(Queen’s Golden Jubilee Medal)。此外,她在2011年與2017年分別以本書及《自由的藝術:歐特克.克提卡的人生與攀登》(Art of Freedom: The Life and Climbs of Voytek Kurtyka)二度獲得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Boardman Tasker Prize for Mountain Literature)。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