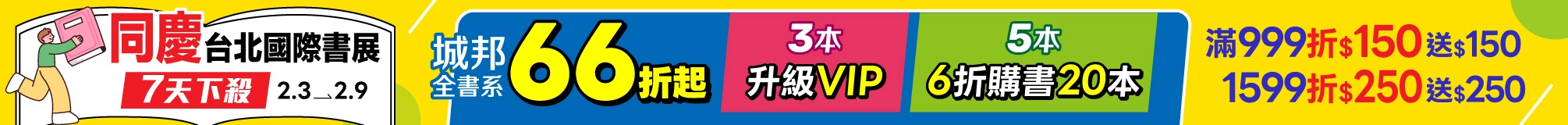沉默的一百種模樣:跨越時代、地域與文化,尋訪關於身體、戰爭、災變、性暴力與精神創傷的無聲告白
- 作者:海莉葉.蕭克羅斯(Harriet Shawcross)
- 出版社:臉譜
- 出版日期:2020-05-28
- 定價:400元
-
購買電子書,由此去!
分類排行
-
律師帶你看校園大小事: 老師和家長必知的44個霸凌防制和性平觀念指南
-
在彌撒中與耶穌相遇:從進堂到禮成,感恩祭的聖經巡禮
-
誰害怕性別?:拆解性別恐懼的幻象
-
告訴我,你是怎麼死的:醫檢處的兩年日常、驗屍檯上的兩百六十二具遺體,菜鳥法醫的血淚養成記
-
共同知識:揭開人類群體合作的邏輯,剖析經濟、政治、日常生活現象的隱藏規則【比爾蓋茲2025聖誕推薦書單】
-
正是時候讀莊子【暢銷經典版】參:莊子的遊心、養身、學愛與自由
-
網路性獵場:從Pornhub到人口販運的暗流──揭露全球最大色情平台的運作真相
-
繼承經濟:是時候談談父母銀行了,千禧世代的獨立難題與社會價值重新排序
-
耶穌比宗教大:我熱愛耶穌,為什麼卻討厭宗教?
-
專家證人:傳奇犯罪心理學者如何揭露人性,為真相與正義發聲
最近瀏覽商品
內容簡介
《私密信件博物館》編輯全新企劃,跨時、跨地探索「沉默」多變樣貌的心靈旅程
最強烈、最切身的感受,為何總是最難以化為言語?
看似百無禁忌的現代語境中,性與死亡何以仍是難以啟齒的話題?
受到戰亂、災難、暴行創傷的倖存者,為什麼在訴說經歷時遭逢重重阻礙?
我們暢所欲言的能力如何被剝奪?又能夠如何尋回?
吳曉樂、林巧棠、陳思宏、陳潔晧——好評推薦
本書聚焦於一個看似抽象、但其實在人際活動中經常出現的概念:不得已的沉默。導致沉默失語的可能原因眾多,包括生理性的腦部異常、心因性的創傷經驗,也有時候是社會規範無形中要求對特定的話題噤聲不語。在這種難以自由使用語言的時刻,人們還能夠如何傳達、分享所思所感?又該如何走出沉默?
作者由童年在學校疑似罹患選擇性緘默症的經驗寫起,爬梳多種語言障礙、失語症狀的診斷史與疾病污名,也觀照自己因為當時失去溝通能力、迴避社交生活而造成的恐懼與退縮,即使在成年後仍然深埋心底,甚至成為她面對親密關係時的阻礙。於是,為了徹底走出回憶中失語的困境,她更廣泛地在文學、表演藝術、醫學史、性別平權運動等領域,尋訪那些受困於沉默之中、卻仍努力將難以言喻之事如實傳達的人物、行動與作品:
——嘗試以「暴露療法」協助緘默症青少年患者的家長和語言治療師;
——因突然失語而被斥為歇斯底里的十九世紀歐洲婦女,以及後世企圖為她們平反的精神醫學與歷史學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中罹患「彈震症」的士兵,與受他們啟發而開創「講談療法」的精神分析學家;
——尼泊爾震災後將心理諮商技巧結合當地宗教文化、引導災民傾吐恐慌壓力的助人工作者;
——傾聽求助者談論絕望與死亡的英國自殺防治機構「撒馬利亞人協會專線」;
——在剛果內戰中遭受集體強暴後,求診修復身體與心靈的女子;
——拒絕委婉修辭、追求真實表達女性身體經驗的革命性劇作《陰道獨白》;
——在麥卡錫主義時代被迫封筆,二十餘年後恢復寫作並獲得普利茲獎的美國現代詩人喬治.奧本……。
以《背離親緣》、《藝術的孤獨》般取材廣泛又結合自身生命歷程的筆法,作者透過史料、訪談與實地考查,寫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如何剝奪人生中特定的情緒或經驗表達的空間。她也更進一步探問言語溝通的極限:訴說悲痛的心情,是否就足以讓人獲得療癒?受害者勇敢道出創傷經驗,是否就能終止壓迫?最終她發現,種種在壓抑之下奮力表情達意的努力,不論是否訴諸語言,都證明了我們的思想和感受能夠以優美、具原創性、甚至充滿震撼力的方式發聲,尋得慰藉與共鳴,並且為更深刻的理解與更具體的行動創造開端。
┤推薦佳評├
當語言過於廣大,渺小的我們該從何開始?說出內心話看似容易,大腦與唇齒之間,卻可能橫亙著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海莉葉・蕭克羅斯從自身「拒絕說話」的經驗出發,親自前往各地踏察,探索各種沈默失語情境的同時,也大膽地回溯了自我的成長創傷。本書的可貴,是她在理解他人生命的同時,更深刻地感受到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連結,也寬恕了個人生命史上傷害的來由。她從冷靜的記者之眼出發,以非虛構的細膩筆法,寫下這本「不說話」的歷史之書。
——林巧棠(作家)
創傷難以敘述,除了社會的誤解,更因為創傷的經歷是難以面對的感受。作者不斷採訪、深究世界各地說不出口的故事,不只是見證傷痛,也是療癒自己說不出口的困難。願我們都有這份勇氣,為傷痛說話,找回聲音,找回感受。
——陳潔晧(《不再沉默》作者)
蕭克羅斯記錄了苦於溝通的人群的生活與掙扎,與他人的交流溝通對他們而言是難以克服的艱鉅挑戰……一段充滿好奇、專注聚焦的探索,深入沉默與孤獨的神祕世界。
——《柯克斯書評》
海莉葉.蕭克羅斯在青春期有一整年的時間無法說話,她試圖理解這段經驗,探討語言的本質……半是回憶錄、半是報導文學,《沉默的一百種模樣》是她嘗試理解人生中那段時期、也理解其他受言語所困的人們的過程,深深觸動人心。
——《衛報》
蕭克羅斯檢視了打破沉默能夠為人帶來療癒的多種方式……《沉默的一百種模樣》引人入勝且知性、發人深省。
——《週日郵報》
將歷史研究和報導文學揉合在一本書的規格內,優美地道出言語的缺席所帶來的效應。
——《金融時報》
極為美妙的閱讀體驗,帶領讀者審視沉默所具有的、時而正面時而危險的力量。
——《愛爾蘭新聞報》
目錄
序言 一把牙齒
.第一卷 恐懼
柏克萊
Volvo車上
一街一幽靈
癲癇的治療犬
歇斯底里與福蠟
詩
長大
說到薯條太濕太軟
.第二卷 性
海德公園
三角點
毛
沉默的共謀
我能幫你嗎?
未封聖之地
利物浦
電話手淫者
剛果之舞
.第三卷 死亡
加德滿都
班加馬提
彈震症
治療心/思
花朵與石頭
沒人會把它印出來的
千魂之聲
震盪
.第四卷 靜默
蘇格蘭
尋找寧靜
深度潛水
發瘋
暗夜
.第五卷 最後的話
這是我,而非我所擁有的
陌生人的臉
授權聲明
謝辭
內文試閱
〈長大〉
事後看來,我緘默的非常時期在一年之內安然度過,算是幸運。很多人無法如此,雖然選擇性緘默症通常對治療反應良好,但是如果不接受治療,沉默的空白童年極可能導致麻煩不斷的成人生活。
許多我訪談過的選擇性緘默症成人患者發展出其他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諸如強迫症、社交恐懼和憂鬱症。
為了一窺選擇性緘默者的日常生活,我花了數週聯繫支援性團體和論壇,但他們的態度模棱兩可。許多人表示願意協助,但多數其實只接受電子郵件往來,打電話製造的焦慮太多了。他們各個都輕描淡寫,是影子般的人,只透過臉書社團互相連繫,但長久以來彼此還是孤立的。他們會寄發長篇大論的電郵,但收到那些首尾俱足的故事,卻沒有來往問答作為中介時,我只覺得這樣做關閉了對話空間,強化了某種控制感。這個過程讓人沮喪,在自己的反應中,我能看見老師被沉默的孩子逼得不知所措而開罵。沉默扭曲了人際關係,而我已對控制習以為常——當記者,就是在說故事與重建別人的故事。他們不會讓我這樣做的。
很多人說到,他們有一股像孩童般的無力感。其中一位是二十多歲的奧利佛,告訴我他以前在學校踢足球的朋友中,有人未曾尋求社交互動。而現在,他也關在自己的房間裡,沒有媽媽代他說話就無法出門。透過電郵,他告訴我:「我覺得自己的年紀比實際上還要小。到了我這個歲數,一切應該要有起色,但我是如此依賴別人。」當奧立佛長得越大,他的溝通困難也隨之加劇,直到現在,他的選擇性緘默有時也讓他無法以非語言的符號溝通。他說:「緊張或難堪的時候,我會僵住。」這通常發生在治療期間,而且「這是難以置信的挫折,我愈發覺得被自己困得死死的,一點用都沒有。」讓人擔憂的是,許多我訪談過的選擇性緘默成人患者跟奧立佛的狀況類似,他們形同癱瘓的沉默每況愈下。珍妮也是二十多歲,目前為進行性緘默症(progressive mutism)所苦。她的狀況時好時壞,在她寄信給我時,她無法跟任何人說話,包括她最親的家人。她唯一的溝通管道是把話寫下來,或「透過她的兔子」貝絲說話。
最後,我終於見到一位媽媽,她願意談論她快要成年的孩子。她們是一對雙胞胎,在我們會面的那段時間,她們除了彼此之外,無法跟其他人說話。雙胞胎比其他手足容易得到選擇性緘默症。在研究期間,我讀過不少令人憂慮的緘默症雙胞胎案例,這次會晤讓我心裡七上八下。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緘默症案例,就屬「沉默雙胞胎」茱恩和珍妮佛.吉朋斯(June and Jennifer Gibbons)。在一九八○年代,還處於青春期的她們就因為縱火案被送進布羅德莫精神病院(Broadmoor Hospital),她們倆只以連父母都無法理解的密語跟彼此溝通。更小的時候,兩姊妹在學校根本不說話,隨著她們長大,也從家人的圈子中抽離,只偶爾跟她們的妹妹說上幾句。有個教過她們的小學老師這樣形容:「她們就像旋進河中渦流的幾根稻草……總是離大家遠遠的,想辦法隱形。」
這對雙胞胎來自威爾斯小鎮上唯一的黑人家庭,在社會上已經遭到孤立。她們溝通的方式是在家中四處留下紙條,請媽媽提供她們需要的東西。根據她們的傳記作者瑪喬莉.華樂士(Marjorie Wallace)敘述,直到雙胞胎姊姊過世,她們的沉默才被打破。一九九三年,珍妮佛從布羅德莫精神病院轉診離開時,死於原因不明的突發性心臟發炎。留下來的雙胞胎妹妹茱恩現居威爾斯,開口談話與常人無異。
吉朋斯雙胞胎擄獲了公眾的想像力,但從現在看來,她們似乎並非有真正的選擇性緘默症,因為她們對說話不抱恐懼。根據傳記的記載,她們的緘默比較像是一個繁複的「童年約定」或一場使壞的「遊戲」,能隨意啟動。這使我不禁好奇,現今的緘默症雙胞胎會跟她們形成什麼樣的對照。
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在一間冰淇淋店跟蘇珊娜碰面。室內有點暖,我的後腿於是黏在光滑的紅色吧台椅上。每當我的話停下來或進行眼神接觸,她就會僵住,攪著融化的奶昔,一根塑膠湯匙讓杯底的藍莓載浮載沉。
蘇珊娜的雙胞胎女兒安和露西剛過生日,她告訴我,她們為了慶生,搭計程車去百貨公司看玩具,家裡有插滿生日蠟燭的水果等著她們。這對雙胞胎極其焦慮,不敢讓任何人看見她們張嘴。她們轉身吃草莓,蠟燭則讓小她們幾歲的表親吹熄。
安和露西現在離開了體制內的學校,上一間寄宿學校,週末回家。回家時,蘇珊娜告訴我,她們只會用一種自己發明的手語跟彼此溝通,只有雙胞胎看得懂。如果要跟媽媽說話,她們會在iPad上打下訊息。這是個讓人十分懊喪的過程,「心情不好的時候,她們壓根兒不會溝通」,蘇珊娜告訴我。「如果我進入她們的房間,她們會拿毯子把自己蓋起來,全都聽她們的就對了。如果我有事去請求她們,倒還像是打攪了。」
和許多緘默症成人的例子一樣,這對雙胞胎的主導情緒是憤怒。「如果她們不順心,無法解釋錯出在哪裡,」蘇珊娜喝了口奶昔,繼續道。「我永遠無法知道她們是否不舒服,或跟彼此吵了架。後來她們開始跟我比那套手語,我看不懂,然後搞錯了,她們便感到挫折。我們從來沒有辦法用說話來處理這些問題,從來沒有辦法解套。她們一直把自己深深埋在某個地方。」
這個家庭以難民身分來到英國。蘇珊娜說,雙胞胎從小就知道必須慎言。「在街上,」她說,「我們不想因為講外國話而被聽見,我們總是怕有人在聽」——就像喬治.奧本在墨西哥提防聯邦調查局一樣。如同許多雙語兒童,這對雙胞胎開口得晚,到了四歲還只能一次講一兩個字而已。蘇珊娜很擔心,於是聯絡了她的醫生,開始無止盡地跟心理醫師、精神醫師、語言治療師及地方上的權威基金會周旋。雙胞胎中的妹妹被定位於自閉症的區間,兩姊妹都被診斷出選擇性緘默症。經過小學時期好幾年的悉心治療,她們都能正常說話了。
然而,當她們上中學時,事態惡化了。就在她們的同儕聊起了男生、嘗試化妝之際,雙胞胎停止說話。蘇珊娜告訴我,她們在開學時得到了放東西用的置物櫃,但不知道開關的密碼。與其開口問,她們寧可天天扛著所有的課本穿過整個鎮,在家跟學校之間來回,直到她們焦躁到委頓乏力。與其徵得同意離席如廁,她們寧可在回家的路上尿褲子,趁忍不住之前在大街上狂奔。但校方堅稱沒有問題,因為她們都能通過考試。因為錯失援助機會,蘇珊娜仍火冒三丈:「她們嘴巴上沒有話,但她們的聲音必須有人聽見啊!這兩個女孩,她們是一言不發地在尖叫求救。當她們低垂著頭走在街上,引起路人注目,如果這不是一種求援的呼喊,是什麼?」
蘇珊娜相信她們閉口不語,是想要停止世界往前急速推進,想避免長大。雙胞胎中的妹妹安說她「會沉默一輩子」。蘇珊娜告訴我「安不想要改變,直到她自己變了,已經無計可施。」現在,她們在家完全依賴媽媽,這個三人組正和世界漸行漸遠。「我離不開她們,」蘇珊娜說,「要是失火了,怎麼辦?她們會說些什麼嗎?」
她用手機給我看孩子們的照片。她們是精靈般的纖瘦孩子,身穿緊身衣,頭戴棒球帽,四處搗蛋。那些照片都是對著鏡子拍的,而不是直接對人拍攝。蘇珊娜告訴我,現在雙胞胎退得離世界越來越遠,她們已經不准她拍照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像蘇珊娜回到她空無一人的公寓,打掃房間和鋪床,為雙胞胎下次回家做準備。現在,我更清楚沉默會為一個家庭帶來什麼,如何把人們拆散,如何扭曲親密關係。不過,我尚未和選擇性緘默症的受害者進行第一手對談過,這份覺察越來越強烈——也許我太強人所難了,竟想和沉默交談。但越是了解緘默症的狀況,越是讓我想和從中生還的人聊聊。
後來,我終究得到機會了。
〈我能幫你嗎?〉
大學時代的第一段性關係結束之後,我茫然失序。我搬到倫敦,接受成為記者的訓練。我會在演講結束後走向戶外的雪中,或呆坐在巴士上,一直到車子開過我要下的站好一段。分手前一年,男友做了一對軀體交纏扭轉的情侶蠟雕送給我。蠟雕是暫時性的作品,他說,是要拿去窯中燒掉的。他說:如果我們結婚,婚後滿一週年他要把蠟雕灌成銅模——就在性愛既潔淨又有價值的時候。一年過後,我把蠟雕裝在塑膠袋裡還給了他。我住在一間臥室牆上有蟎的窄小公寓裡。花園長了叢繞著報廢汽車生長的黑莓灌木,在十二月乾晴的下午,狐狸會去那裡曬太陽。那是一間沒有客廳的公寓,我的生活感覺彷彿徹底崩垮、摺疊進臥室的四面牆中間。
我埋首工作。現在回想起來,我在那個時期的自己看見了一些伊芙的影子——跑到世界的盡頭去聽別人的故事。有段時間,我在工作上來者不拒,照單全收。我去了阿富汗,五年間去了四次。我還記得第一次去的前一週、上那堂「艱困情境課」的時候。我們遭遇模擬恐怖攻擊,我在暗中摸進一個地下室,周圍被槍聲圍繞,我得找到扮演受傷記者跟平民的演員,滿手都是假血。我學會了如何處置抽動的胸腔傷口,和用三件外套製造簡易擔架。下課的晚上,大家在酒吧用笑聲消化掉這一切,但我真的被震撼了。有個聲音在問我:「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我希望有人發現,然後問我好不好。
分手後的那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間新聞公司值班,去法庭見證別人的人生分崩離析,徹夜開車前往火車事故現場。由於工作是輪班制,我發現手頭上有不少時間。我會在早午間看電視,中場廣告是助聽器跟地中海遊輪之旅,然後錯過晚上外出的機會,因為要去辦公室。我的輪休跟別人對不上,我得找事做打發時間,所以我有不少思考的餘裕。有天早上,我在地方報紙上看見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廣告。他們在徵求志工,尤其是可以在日間或深夜幫忙的人——那可是寂靜跟孤寂最張牙舞爪的時候。有一天早上舉辦說明會,我就去了。
回顧那段日子時,我想到伊芙的箴言:你應該「給予別人你最需要的東西」。在那些狹隘又孤獨的日子裡,我需要被同情。重讀那個冬天寄給前男友的電郵讓我瑟縮成一團,憤怒在頁面上慢慢燒起來。我需要幫助,去面對無法控制現狀的深刻哀傷。無法得到足夠的愛,或無法聽取他的解釋,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但我從未得到我需要收到的慰藉。
回想起來,在我恢復單身的第一年,撒馬利亞人協會讓我能夠給予別人我最為需要的東西:同情、時間跟注意。在撒馬利亞人協會,我生平第一次學到真正的溝通長什麼樣子,如何傾聽,如何被聽見。
作為新進志工,我們被教導服務的目的是去傾聽他人,不帶評價也不給建議。我記得在受訓的第一天,我們和一個裝扮成洗衣機的男人進行了一場練習。練習的概念是,他扮演來電的人,讓我們體驗當撒馬利亞人的感受。我們圍成一圈輪流。隨著狀況逐漸明朗,他的問題是他的洗衣機壞了,我們這些新手則要想辦法找到解決之道:「你想過要打給水電工嗎?」或「你能不能去附近的洗衣店?」但這些解決問題的提議於事無補,只讓他往厚紙板機殼的內部越縮越深。
較有經驗的撒馬利亞人協會志工對他提問:他是怎麼因應的,或沒有洗衣機,最難受的事情是什麼,唯有此時他才漸漸從機殼中浮現出來。接著,我們就聽見了一段長期遭受孤立的生命故事,關於失去和對自己的憎惡,因為連這麼簡單的事情也處理不好。他講起自殘跟飄忽的自殺念頭。我從來沒聽過這樣的對話——世界好像正在掀開。然後呢,終於,才是如何跟別人對話的守則。面對接下來的星期,我們獲取了傾聽他人的技能裝備。那些裝備讓我們懂得去呼應或簡述別人講的話,求取更多資訊或解釋,或純粹提供鼓勵的聲音。重點是當個人,說自己聽起來覺得自然的話,讓談天歸談天。然而,這跟多數的會話——或應該說我的會話——的發展模式都不一樣。我們被鼓勵去伴隨他們進入即將鋪陳開來的沉默,而非將他們拖進自己熟悉的範圍,或告訴他們「振作點」。
我記得那些坐著的深夜,聽著人們對我訴說他們的不可告人之事,因為他們怕被送進精神病院,或怕沒被聽見。我不被期望去提供意見或答案,這點我滿喜歡的。很多時候,我們就只是坐著不說話。但是呢,撒馬利亞人協會開宗明義告訴會員,我們不能透露電話內容,所以我不能寫出自己接過的電話,或其他志工跟我轉述過的談話。我再度繞著沉默打轉,好像在做研究時嘗試跟選擇性緘默症的患者對話一樣,他們只會用電郵回話。
情勢所逼,我開始找尋將自己的故事分享出來的來電民眾。我找到了一位名叫蘇菲的女子,她曾在一九八○年代聯絡撒馬利亞人協會,將經驗紀錄在自傳《傷痕歲月》(Scarred)中。她第一次打電話給撒馬利亞人協會,是在電話亭裡。她當時十四歲,從十二歲開始被養父性侵。養父先對她下手,然後邀朋友到她兒時的臥房集體性侵她。她的反應是自殘,但一被爸爸發現她在割自己,他竟跟著加害——在她身上捻香菸,評論她如何享受痛感。她繪聲繪影地描述自己有好幾次如何想結束生命,有次是在十五歲時,她發現自己懷上了養父的小孩。她已經因為他懷孕過一次了,知道自己無法再承受另一次墮胎,所以跟主管機關謅了個「男朋友」的故事求援。她的人生是一道「自殺螺旋」,看起來無路可逃。
她在書中說撒馬利亞人協會無疑是她的救命恩人。經歷一晚特別邪惡的強暴後,她第一次打給他們。從此以後,她和兩個撒馬利亞會的志工成了「朋友」,他們在她的少女時期持續保持聯繫。在一場B B C世界新聞的訪談中,蘇菲表示正是撒馬利亞人協會的保密讓她能把他們當作「放心的地方」。在那裡,她能吐露不能告訴別人的事情。她表明,萬分重要的是,她要確定沒有人會「突然闖進來」拯救她,或把她從爸爸那裡帶走。他灌輸她的觀念是,她是被收養的,而在這個世界上,她就只有他了。想到會失去他或讓他失望,比被強暴還糟。所以,唯有知道跟撒馬利亞人協會的聯絡嚴格保密時,她才有辦法坦誠講出自己的遭遇,講出她感受到的絕望,同時不用擔心會有社福救濟介入把她帶走。
蘇菲想和養父待在一起這件事,看起來頗為反直覺——但透過他們不評價跟保密的原則,撒馬利亞人協會在其他支援管道都失敗時,成功提供了支柱。最後,蘇菲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被送進了一間安全的精神治療機構,因為她已經對自己構成威脅。在那裡,她開始了漫長的恢復過程。出於深深的感謝,她出院後加入了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志工團隊,成為分會會長,然後在二○○八年到二○一一年擔任全組織的主席。
和蘇菲一樣,我知道撒馬利亞人協會跟其他組織不同之處,在於他們重視保密性跟不求解答、不做評價的傾聽。我進行過許多談話,聽見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同時驚訝於純粹不提供解套的方式如何能幫助人們講得更多。我常常希望小時候的自己曾經打給他們。參加志工訓練時,我在陷入低潮之際偶爾也會打給撒馬利亞人協會,聽話筒另一端的聲音說:「撒馬利亞人協會,我能幫你嗎?」我從來沒回話過。靜靜和一個人坐在那裡幾分鐘,已經夠了。
作者資料
海莉葉.蕭克羅斯(Harriet Shawcross)
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非虛構創作學程碩士,曾擔任記者、導演、製片人,專長為人物訪談故事報導,曾與BBC、《經濟學人》等媒體合作,遠赴阿富汗、尼泊爾等地報導戰爭與震災的衝擊,途中所見當地人民與創傷後遺症共存的歷程,促使她對「沉默與表達」的主題深入研究,繼而寫下她的第一本書《沉默的一百種模樣》。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