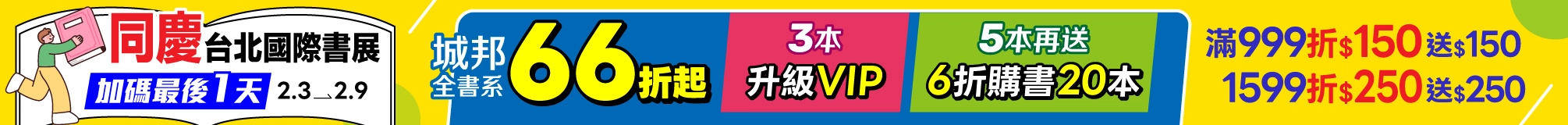內容簡介
「在金錢和權力的面前,
人類只能成為追名逐利的野獸!」
縱橫日本文壇.跨越世紀巨匠 松本清張
寫盡亙古不變的權力鬥爭
氣勢萬鈞的中亞、東亞古代史推理結晶
黑暗的學界惡鬥.曖昧的盜墓軼事.天皇身世的大膽顛覆
一名睿智的女子,吹開籠罩歷史的千年迷霧
一顆七世紀的神祕巨石,引出日本與波斯的邂逅
兩代追求相同目標的靈魂, 輝映光和暗的豐富人性
【內容簡介】
一道巨石的謎題,一次街頭的刺殺,
女子的肩頭,擔起回溯千年的歷史之旅,
她踏上探索日本身世、燃燒夢想的傳承之路……
更不經意撩撥起、學界塵封已久的殘酷鬥爭!
高須通子,史學界的年輕明星,大膽作風讓她難獲學界青睞,她不顧他人眼光,獨自研究叫「酒船石」的神祕石頭。一場奈良的刺殺,結識了身世不明的男子海津信六,撕開數十年前的學界醜聞,引出「拜火教」和天皇的傳奇軼事。通子為了解開日本和異國的千年之緣,遠赴伊朗,但料想不到的心魔追上她的逃亡……
海津信六,學界鬥爭的落敗者,他過去身在象牙塔的漩渦,清楚古董店、盜墓者、史學家和宗教團體之間的骯髒關係。當年,他含恨退出,多年後,埋葬的夢想、學界醜聞、盜墓軼事,和他私密不堪的愛,都在一場刺殺中,如他的鮮血汩汩而出……
兩代人生的奇蹟交會,未竟夢想的動人傳承,高須和海津可否重拾自己的人生?
齊明天皇的身世謎團、酒船石的祕密,如何揭露東亞和中亞文化的前世今生?
學界、盜墓者、古董商和新興宗教的恐怖平衡,將牽扯出撼動政界的驚人醜聞,
在人人自身難保的鬥爭世界中,這些利益勳心的人們,何去何從?
伊朗通往日本的路,在權力爭鬥中,是殆盡夢想的灰燼之路;在思想的傳承下,是燦爛的文化之路。《火之路》寫下真實恐怖的人性篇章,更是日本昭和世代最偉大的小說家松本清張耕耘古代史的光輝結晶。
【本書特色】
◎松本清張的兩大特色!結合人性糾葛、學界鬥爭,以及古代史推理的文學結晶!
◎清張爬梳正史、野史、宗教經典和論文,加入歷史人文的觀察,重新詮釋日本、伊朗、拜火教、佛教、日本天皇的傳說軼事,輔以古董商、盜墓者、贗品製作者和學者之間,既是依存又是鬥爭的黏膩關係,編織出驚心動魄的古代史推理!不僅讓人為浩瀚的歷史而動容,也呈現清張淵博的學識、驚人的洞察力、豐富的想像力和厚實的筆力。
【經典推薦】
◎林長寬(政大阿拉伯文系/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賴振南(輔大日文系教授)
「瑣羅亞斯德教,或稱祆教、拜火教(金庸小說中的「明教」)是否經由中國傳入東瀛落地生根,學術界無明證,但有推理。松本清張大師的《火之路》雖是推理小說,亦是學術研究的推理,尤其是中亞與東亞的宗教流通史。藉由歷史的推理,松本清張也批判了日本大學名校的學術黑暗面,令人讀起來心有戚戚焉。作者的引經據典對宗教文化史有興趣的讀者有入門引導作用。」
——林長寬(政大阿拉伯文系/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內文試閱
坂根要助那天中午和高須通子在奈良縣政府前的路上巧遇,還和通子一起去醫院捐血給被吸毒者刺傷的男子,關於這件事,福原並未從要助聽聞隻字片語。如同要助先前對通子所說,要是福原得知此事,不僅會笑他此舉古怪,可能還怪他浪費時間,因此一句話也沒提。要助雖是自由攝影師,不過在跟著雇主展開攝影旅行的期間,得受出資者時間約束。
因此,當佐田提到案件,福原以為他說的是當天傍晚在奈良的巧遇。但佐田端正的臉龐與平時冷峻的表情不同,顯出激動之色。「我在報上看到那起案件的報導,發現一個很稀罕的人名。」佐田銀框眼鏡下的雙眼瞪得老大。
「哦,怎麼說?」福原隨口附和。
「報上提到一位被害人的名字叫海津信六。他沒被殺死,是身受重傷。你記得這件事嗎?」
「名字我不記得了,好像有兩人身受重傷,對吧?」
「他是其中一人。男性,五十八歲,保險業務員。」
「保險業務員這幾個字,我稍微有印象。」
「就是他。」佐田說,平時總以低沉聲音說話的男子,難得聲音高亢。不過他靠向椅子的上半身靜止不動,這是他平時的習慣,此刻同樣維持姿勢不動。「就是他,海津信六。好久沒看到這四個字了。」佐田一副大為感動的模樣。
「是老師您的朋友嗎?」
「不算直接的朋友。」佐田回答,沒再接話。他的老毛病是喜歡吊人胃口。接著他自言自語:「……不過,我都不知道他在大阪附近當保險業務員呢。要不是這次的案件登上新聞版面,我恐怕都不知道。」
「不會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吧?」福原當自己在和他聊天。
「同名同姓是吧。」佐田聽完福原的說法,煞有其事地側頭尋思,嘴角帶著一抹笑意。「……剛看新聞報導,我也這麼想。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簡單來說,翻開東京地區的電話簿,同名同姓的人好說四、五個。不過,海津這個姓氏不常見。我的佐田也算少見的姓氏,但久男這名字就很普遍。不過信六這名字可就不常見。你看,海津這個姓很罕見,信六這名字也少有,這樣的姓名組合不太可能有同名同姓的人出現。」
「原來如此。」福原頷首。
「還有年齡。這個要素再符合,是同一個人的可能性又更高了。」
「他的年紀……好像是五十八歲?」
「沒錯。現在我不知道他的正確年齡為何,不過大致是這個年紀。」
聽他的說法,可以想像佐田很久沒和海津見面。但佐田很確定他是自己認識的人。福原覺得連輕鬆問一句「請問他是什麼人」都不太恰當,於是他問:「職業呢?報上寫他是壽險業務員……」
「這點倒完全不同。不,與其說不同,不如說是意外。」佐田藉由口吻來強調意外。
「聽您這麼說,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職業嘍?」
「就那時候來說的話。」
佐田視線望向地面,看起來無限感慨。不過話說回來,說話時總表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是佐田的習慣,福原無法從他的神色來猜測他到底是何心思。他說的那時候,是很久以前嗎?福原還沒開口問,佐田倒是先說了。
「報上提到海津信六住在大阪府和泉市。雖然和泉市我沒去過,但那應該算大阪裡一座田園都市吧?」
「我也不太清楚,應該是。」
「與其說從都市搬往鄉下,不如說是落魄躲到鄉下。上面說他當保險業務員對吧。這也很像他後來的形象。」
「海津信六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人?」福原再也按捺不住。
「他是位史學家。不,應該說他曾經是。如果現在他仍待在學界,想必會是很了不起的大學者。」
「您說海津信六先生是位史學家?」
聽佐田這麼說,福田大為吃驚地反問。由於音量頗大,佐田銀框眼鏡下的雙眼慌張地環視。接待室裡的桌子還坐著其他兩組人。一旁的那組人看起來像某家出版社在提美術出版的企畫案,社員將計劃表攤在桌上,與一名中年館員討論。他們談得正起勁,似乎沒聽見福原的驚呼。
「抱歉。」福原搔著頭。
佐田將自己的椅子靠向桌子,平時神色倨傲的他,難得採前傾的姿勢。「你這樣我很困擾,難保不會讓人聽見。」佐田壓低聲音警告。
「是,對不起。」福原一臉歉疚,跟著將椅子靠向桌子,湊向對方。
「要是有人知道海津信六這名字,就會豎起耳朵偷聽我們談話。」佐田目光又掃向一旁。
「真的很抱歉……對了老師,剛才您提到,要是海津先生仍待在學界,現在已是很了不起的史學家,是嗎?」福原小心翼翼地悄聲問。
「沒錯,我這麼認為。」
「我對學界的事不太熟悉,不過,海津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史學家嗎?」
「他曾經是。因為現在不是。」佐田糾正福原的說法。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麼嘛,大約是二十年前,當時他從學界消失。」
「二十年前?」
「所以我也沒見過海津先生。當時正好是我大學畢業那時候。不過,我從專業雜誌上得知他的大名和學問。也聽前輩提到他,在我們這群年輕同伴當中,常提到海津先生。說得誇張一點,我們對海津信六這名字懷有敬畏之情。一來也是當時我還年輕。年輕人的憧憬之心特別強烈。」
「這麼說來,以現在老師您的眼光,海津先生的學問並不像當時人們對他的評價那麼高,是嗎?」
「不,沒這回事。就算以現今來看,他還是很了不起。雖然半途退出學界,未能有大成之作,但不論是研究的著眼點、深度,還是構想,都敏銳非凡,時至今日仍充滿啟發性。像他那樣的天才人物,後來一直沒再出現。」
福原在口袋裡掏找打火機。難得誇人的佐田,竟對二十年前從史學界消失,目前在大阪府當保險業務員的海津信六讚譽有加,還用「天才」這樣的字眼,令福原也產生興趣。得知海津的契機,是發生在當晚他們過夜的奈良的一起吸毒犯傷人事件的新聞,這令他感覺與自己關係密切。
佐田從口袋取出菸斗,叼進嘴裡,湊向打火機的火焰。這時,隔壁桌的人結束談話,訪客走出接待室。還剩另一組人,但與他們隔著空桌,正輕鬆交談,朗聲大笑。
「海津信六在學問上極敏銳。就如我剛才說的,他消失得太早,沒留下正式著作。這是他自己的意思,在準備階段就這麼結束。但看過他在專業雜誌上的論文就知道裡頭極具啟發性。對學問充滿遠見。就這點來說,他就像是預言者。」
佐田聲音輕細,對海津信六大為誇讚。
「哦,真那麼了不起?」
「你或許以為我講得太誇張……」
「不,既然連老師您都這麼認同,那真的很了不起。」
「因為這是事實,無從否認。雖然不能大聲說,但在現今史學界教授級的人物中,有人根據海津信六的論文來發表自己的論文,佯裝成是自己的看法,連臉都不會紅。像這種事,我在奈良的寧樂堂沒提到嗎?」
「是。」
這是指老師大剌剌盜用學生論文。學生將自己在學界的未來全交給老師,即使有牢騷也不敢發,只能暗自哭泣。佐田指出這是學界的「慣習」。
「沒有哪位學者敢直接盜用海津信六的論文。但由於海津的論文極具啟發性,用來當論文的主軸再適合不過。」
「不過,真那麼做的話,不是看得出當中用的題材嗎?」
「知道海津信六論文的人會推測出這位老師的學說是用他的題材。但沒被公開批評,是大家都幹同樣勾當。」
「像這種情況,不能將作為論述基礎的海津先生論文列為參考出處嗎?」
「哪能這麼做啊。」佐田將菸斗移開嘴邊。「……幾乎沒有哪位學者想公開此事。因為全是一些沒自信的人。況且要是提到海津信六的論文名稱,只會造成減分的效果。」
「為什麼列出海津信六先生的論文會造成減分效果?如果真是天才型學者的論點,應該會有加分效果才對啊?」
福原提出門外漢的質疑。
「在學界裡,這種正確的言論行不通。因為有派系。這你也是知道的,不論多麼權威的學者提出的論點,反對派的學者也絕不引用。若有學者引用,肯定會被自家學派的人圍剿。更何況海津信六是年輕時便退出學界的學者。要是明確寫出自己引用他的論文,下場一定很慘。」
佐田玩弄著菸斗,一會移開唇邊,一會又湊上。
「以他這種學者的論點作立論基礎,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嚴重的矛盾。這樣的矛盾暢行無阻,正是學界的特殊性。簡言之,現今的學者、學院、研究所教授、副教授、講師,思想都太貧乏,非得借助海津信六的想法。」
聽佐田的口吻,福原想起他在奈良古董店對T大的久保教授及板垣副教授的批評。與其說批評,不如說講他們壞話。對面桌的那組人,談笑自若地站起身。待他們消失後,寬敞的接待室只剩佐田與福原。
「海津信六先生退出學界的原因是什麼?」
現場已無旁人,福原略微提高音量。佐田也變得輕鬆些許。他將菸斗擱在桌上,摘下銀色的細框眼鏡,以手帕擦拭模糊的鏡片。
「海津信六要是仍待在學界,現在那些教授都將為之失色。」佐田並未直接回答福原。
「真有那麼優秀?」
「與其說優秀,不如說驚人。沒錯,是驚人。舉例來說,當其他人還走在實證的路上苦幹時,海津信六早領先一、二十步了。遲來的實證型結論,一直在他的天才遠見之後苦苦追趕。」
「求學問不是很尊重實證嗎?」
「沒錯。沒實證性的學問,稱不上學問。但近來所謂的實證,和資料羅列沒兩樣。這是沒才能的學者刻意將兩者摻和在一起。如同我在奈良時提過的,板垣副教授只是以其他學說當資料來介紹,完全沒提出自己的見解。老師應該認為這具有實證性和科學性。但我認為這是假的實證主義,除了暴露出當事人的無能,沒半點用處。話說回來,板垣上頭的久保能之教授也是如此。人們說他是穩健型的學者,但所謂的穩健,可以直接以無能來代換。正因無能,構想才無法往外延伸。只會一味鞏固自己的守備範圍。世人都說這是久保的穩健或謹慎作風。副教授板垣也有樣學樣。久保教授被人批評也沒辦法。他原本並非史學出身,而從法律領域跨足而來,才成為現在的教授。」
由於已無旁人,接待室只剩他們,佐田的口吻平靜許多。他將美式銀框眼鏡擦拭乾淨,重新掛回他高挺的鼻梁,接著仔細擦拭菸斗。
「久保教授是法學院的人?」福原望著佐田眼鏡的亮光問。
「咦,你不知道?」
「他開設古代史的課程,我一直以為他是文學院史學系出身的。」
「從法學院時代起,久保便是透過法制史展開古代和上代的研究。他的專業應該是律令制度。大化革新、近江令、養老令之類。在古代,有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刑法制度論文。例如提到須佐之男命被逐出高天原時的罪刑,是部落共同體的村八分制裁,或是『千位置戶』意指沒收財產的懲罰,這都是常識,卻說得臉不紅氣不喘,都在說些很理所當然的事。把無關緊要的瑣碎事羅列出來,拉拉雜雜講一堆和主題無關的內容,這是實證主義?這根本就是炫耀才學的虛飾手法,掩飾自己貧瘠的一種詐術。」
佐田平靜的語調隨著激昂的情緒上揚,還參入一絲論文的口吻。
「久保就是這種人,都用這種手法。古代的罪刑,要是遇到像祝詞裡出現的天津罪、國津罪,他便完全沒轍。直接將民俗學的人說的話拿引用。說起來,將民俗學想成古代歷史學的輔助學問或相近學問,正表現出他的無知。民俗學和其他學問差得遠了。人們都說民俗學欠缺歷史性,我很認同這點。久保認為,要是引用折口信夫迷信的直觀說,對此崇信不疑的民俗學者會高興不已,正可強化他的論點,真是可憐的男人。他所謂的古代法制,只侷限在日本,所以搞不清楚通盤狀況。說的淨是無知的內容。由於他沒進一步了解古代朝鮮、北亞、東亞的民族習慣,所以講的全是前後矛盾的事。要指望他寫出好論文本來就不可能。因為這樣的大學教授,整個大學的水準都降低了。」
菸斗開始綻放黃褐色的光澤。
「關於久保教授的無能,就講到這兒。」佐田滿意地端詳光澤亮麗的菸斗,抽口菸後,緩緩接著說。「……傷腦筋的是,他完全沒發現自己的無能。以為做學問只要用自己那套實證主義就行了。因為沒人提出批判,他一直都不懂這個道理。」
「為什麼不批判?」
海津信六退出學界的話題,聊到一半突然中斷。福原很想問清楚,但要是催佐田,打斷他的話,搞不好會惹惱他,所以他還是保持沉默。不過,久保教授的事倒也挺有意思。
「第一,就算想批評,久保的論文羅列許多資料,無從批評。對資料沒新的解釋,也沒自己的意見。這樣根本無從挑剔。」
「原來如此。」
「第二,學者之間,私底下怎樣姑且不談,表面上都表現得謙恭有禮,很尊崇對方。儘管背地都稱對方『那個傢伙』,但在公開場合一定都很客氣地尊稱對方久保教授或久保博士。尤其在爭辯後更是如此。相當慇懃有禮。」
「嗯。」
「這麼一來,感覺遲鈍的傢伙會更遲鈍。」
「是這樣嗎。」
依福島擔任編輯的經驗,對方在說人壞話時,絕不能表現深有同感。頂多只能笑而不答或是點頭。否則會被對方當作同一陣線,日後要是讓當事人知道,恐怕惹來怨恨。福原基於這樣的經驗,很消極的以「是這樣嗎」來附和。
「就是這樣。」佐田再次確認。「……不過,久保也有他自卑的地方。他不是文學院史學系出身,而是由法學院跨足。說到史學教授,終究還是以史學系出身的人才算正統。這是他暗藏心中的苦惱,也令他有種自卑感。」
「原來如此。」
「提拔久保到今天這個地位的人是之前的主任教授,如今擔任榮譽教授,仍精神矍鑠的垂水寬人博士。垂水先生的個性寬洪大度,不拘小節,才能成為學界領袖。心思太細膩的人當不了領袖。」
「哦,這樣啊。」
「當然是這樣。所以久保當不了領袖。垂水先生不擅長古代法制,才對久保賞識有加,將他拉進自己的派系。」
佐田的話題全繞在久保教授和板垣副教授。雖屬同樣大學體系,但東京美術館的佐田位於「局外」,對「總部」大學學院頗有偏見。因此,總是持旁觀者口吻的佐田一聊到學院話題,自然特別起勁。不過,關於久保教授和板垣副教授的話題,福原也頗感興趣。
「垂水教授擔任學校主任時,將久保拉進自己的派系裡,想扶植他當接班人。因為垂水教授就是這種大剌剌的個性,不拘小節。」
佐田接著說道。
「……久保幸運的是,垂水教授視為接班人,眾人也都認同的折原政雄副教授因病亡故。若不是這樣,就算久保再怎麼忠心服侍垂水教授還是當不了接班人。垂水教授也不能那麼做。」
「這樣我大致了解事情始末了。對了,關於海津信六先生當時的地位,從年齡來看,應該比垂水教授小幾歲吧……」
「當時垂水教授擔任副教授,海津信六先生是助教。教授是山崎嚴明先生。」
「啊,那位有名的山崎嚴明教授。」
「從現今的眼光來看,這位教授的格局還是一樣恢宏。不單只在他專業的學問,對考古學、佛教美術、人類學等領域,他也常發表意見。而且頗有見識。明治到大正初期的學者都很偉大。近來由於專業細分化,格局愈來愈小。」
「請問……助教時代的海津信六先生……?」
「海津信六並非國立大學出身,也沒上私立大學。他是地方高等師範學校出身。」
「咦,這樣啊?」
「他的故鄉好像是岡山縣津山。擔任過舊制中學的歷史老師。他常寫歷史論文寄給山崎教授。山崎教授看過後認為有可看性,聘用他到自己的大學擔任助教,讓他鑽研學問。當時垂水寬人先生是副教授。就年紀來說,垂水教授長海津信六先生八歲。」
佐田抬起頭,像從記載海津信六今年五十八歲的那篇報導往回推算般在回憶海搜尋。窗口射進的陽光,照得他的銀框眼鏡反射白光。
「海津信六上頭還有折原先生,是他的助教前輩。但副教授垂水和助教折原都比不上海津信六。垂水先生對史料的鑽研不夠,折原先生勤奮好學,但缺乏獨到見解。山崎教授對海津信六青睞有加。因為他的資質遠非其他人所能比……」
佐田似乎忘了說過久保教授和板垣副教授的壞話,改談海津信六,福原心情登時輕鬆許多。聽他批評當前學界的學者,畢竟還是很尷尬。
佐田吐出一口白煙。
「當時海津信六常寫論文。刊登在史學系所屬的學術雜誌《史學叢苑》上。這在現在很難想像,但當時的學界仍是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是,海津信六有山崎嚴明教授的推薦。《史學叢苑》的編輯委員全是教授學生,所以不會有任何意見。沒人敢抱怨半句。這令垂水先生和折原先生的處境尷尬。」
「因為這個原因,山崎教授過世後,海津先生就被趕出學校是嗎?」
這是常有的事,所以福原如此問。
「失去山崎教授這座靠山的海津信六,很難繼續待在大學裡。因為教授是他唯一的庇護人。不過他在外面也有少數支持者。例如與T大對立的私立大學。打從山崎教授仍健在的時候起,海津信六的論文不僅在《史學叢苑》刊登,也常見其他大學的專業雜誌,就是這個原因……如果是現在,實在很難想像。如今勢力範圍明確,壁壘分明。以前的學者度量大多了。」
「海津先生被趕出T大後,不得不從學界消失是嗎?」
「才不會這樣就消失。說起來,當時他的論文並未公開獲得好評。大家都只是默默閱讀。對他提出的證據感到欽佩或是敬畏。也有人批評他的想法太前衛。從那時起,海津信六就有一種超越的傾向。但他並非是個人的胡亂猜測,完全根據史料表示意見。他對史料的批判也相當嚴格。絕不像部分學者那樣,只從史料擷取自己想要的部分,或用自己的解釋來自圓其說。當時被認為很前衛的海津論點,在後來研究的進步下,已被現今的學界承認。」
「海津先生這麼偉大啊?」
「真的很偉大。可惜沒寫出正統論文。全是雜誌的小論文,沒歸納整理。目標對象也太多。這是最可惜的地方。要是他在學界待久一點,應該會寫出更正統的研究著作。要是海津信六還留在大學,恐怕連垂水教授也沒辦法那麼安穩,更別提久保教授和板垣副教授的出現根本就是痴人說夢。」
「……」
「他們是無能二人組。久保懷有一種自卑感,所以對板垣很冷淡。」
佐田又將話題拉回久保教授和板垣副教授身上。再這樣下去,根本問不出海津信六「退出」學界的原因,福原有點焦急。但佐田對這個話題相當熱中。
「說到久保教授為何對板垣如此冷淡……」他手握菸斗。「……就像我剛才說的,久保是從法學院跨足史學系的異類。換言之,他非正統派出身。對文學院史學系出身的板垣有種自卑感。久保教授長期以來一直只讓板垣當一名助教。」
「連講師都不讓他當嗎?」
「板垣去其他大學時,為了讓他能在那裡取得副教授資格,才昇他當講師。但只有很短一段時間。」
「板垣先生曾到其他大學擔任副教授,是嗎?」
「沒錯。板垣長期在久保教授下當助教,備受冷落。學生都半帶嘲諷地叫他『坂垣大助教』。那時起,就有人說久保對板垣很冷淡,都不照顧他之類。後來連久保也覺得不好意思,像剛才我說的,讓板垣到同體系的其他大學當副教授,一年半後又讓他重回自己門下。久保的個性很神經質,他很在意別人怎麼想。對板垣這樣處置也是這個緣故。」
「原來如此。」
「正因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助教,板垣終於否極泰來,現在對久保教授可說是畢恭畢敬。久保教授是個對假實證主義極為謹慎小心的無能學者,板垣也不能太搶鋒頭而搶了久保風采。他一味地顧忌久保教授,小心翼翼不讓自己跳脫久保的研究態度範圍。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板垣想搶鋒頭,他也沒那個能耐。」
「久保教授對自己是來自其他學院這件事,真有那麼自卑嗎?」
「原本官僚主義就是這麼回事。講究血統純正。儘管出身的好壞和學問研究一點關係也沒有。」
「就是說啊。」
「不,話雖如此,如果久保教授是位優秀的史學家,我們也會對久保的自卑情節感到同情,但這位久保教授可不是這樣。以人類考古學來說,也有醫學院的教授得到眾人好評的例子。這是學問的性質使然。但史學可不是這麼回事。特別是久保專攻的古代法制史,根本就無用武之地。」
佐田將熄滅的菸灰敲向菸灰缸,開始整理菸斗,這時他像突然想到似的說道:
「對了,之前在奈良古董店遇見的女子,叫高須通子的助教。她呀……」
佐田提到高須通子的名字後突然打住,因為這時剛好一組人走進接待室,但他可能看準對方是可以放心的人,壓低聲音接著說:
「……她跟在久保、板垣底下,真教人同情。她是位才女。上面全是無能的人,就算想展現才能也會被打壓,有志難伸。被人壓一塊重石頭在頭上。在奈良時,雖然我一再挖苦他,但她擁有很獨特的構想。」
「您和高須小姐談過話是嗎?」福原在腦中想像通子的模樣。
「我看過她寫的文章。」
「一樣是在《史學叢苑》上嗎?」
「那裡像傳統權威的象徵,其實全是副教授和講師們的舞台。教授等級的人,偶爾會在上面寫幾篇文章,執筆者全是教授在後面撐腰。助教也會在上面寫文章,但她的風格與眾不同。她很少在那裡投稿。高須通子的名字常見於民間的歷史研究團體雜誌、以出版歷史書為主的出版社專業雜誌,或像同人誌的研究雜誌。」
「為什麼?」
「如果她是個向頂頭上司討好的助教,應該會拿自己的文章請他們過目,或是刊登在《史學叢苑》上。但如果是在外部雜誌上發表,則可以隨自己高興。因為她很有自信。」
「這麼一來,久保教授和板垣副教授會不高興吧?」
「這是當然。與其說是默認,不如說是漠視。一來也因為她是女人。」
「因為她是女人?」
「久保教授還有另一位親信的男助教。常往久保的家裡跑,負責整理史料和處理雜務,甚至還幫忙跑腿處理家務。久保沒要讓高須通子成為接班人的意思。高須通子自己應該也沒那個意願……」
「她採取消極的抵抗嗎?」
「與其說是抵抗,不如說這種生活態度是現代年輕人的普遍性格。以前那種徒弟擁有使徒意識的師徒關係漸趨淡薄。除了那些追求功利的弟子以外。」
「這麼說來,身為助教的高須通子,其實沒接受久保教授和板垣副教授的指導嘍?」
「指導?」佐田的銀框眼鏡閃過寒光。「如果是那位親信的助教,我就不知道,但要是高須通子,根本就沒受過任何指導。」
「教授們都沒照顧她嗎?」
「應該說是沒辦法照顧吧。她特異獨行。不同於一般研究生,身為一位未來的學者,她已獨當一面。而且還是位才女。」
「史學系研究室的情況我不熟,但醫學院的教授不是會給助教定研究主題,加以指導嗎?難道他們沒有?」
「沒有。醫學系採共同研究。透過研究的細分,多的是可以丟給助教研究的小主題。助教就像教授的僕人,幫忙打雜。史學系則不然。以久保教授來說,他許多時間是以兼任教授的身分到私立的V大學兼課,幾乎沒在T大露臉。似乎在V大比較愜意。就算助教高須通子到研究室,也很難見得到久保教授。」
「那板垣副教授呢?」
「哦,說過很多次了,他根本就一無是處。只會看久保的臉色,他全副心思都在久保身上。」
「高須小姐只是去研究室看史料嗎?」
「史料?真正值得看的史料,會在研究室或大學圖書館嗎?那些上代史、中世史,特別是現代史,重要的史料和資料不是在教授個人辦公室上鎖的書桌,就是擺在自家的書架內。這些重要的史料和資料,要是讓助教或學生窺見,教授的地位便岌岌可危。因為教授藉由擁有這種史料,保住研究者的架子。當然了,購買這些史料,用的全是大學的經費,如果是公立大學,花的是人民的納稅金,倘若是私立大學,則挪用學生和家長的錢。像這種公私不分的情況真夠了,而且史料本來就應該讓所有研究者看,但久保和板垣這些人,除了將它們據為己有,根本想不出其他辦法來彌補自己實力的不足。」
「這樣啊。」福原低語。
「如何,很驚訝吧?」佐田朝他冷笑。
「真的很驚訝。」
「學院外的人或許會很驚訝,但這在學院內算是人盡皆知的事。大家早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大家都麻木了。高須才得獨自四處找尋史料和資料。她兼差當高中的鐘點講師,趁空檔時間做研究,真是辛苦她了。」
剛才走進的那組人坐沒多久便離去。
「對了,老師。」福原見佐田談大學相關的事告一段落,改問他一直想問的問題。眼下正是發問的好時機。「海津信六先生為什麼會從學界消失?」
佐田上身斜靠一旁,單手手肘倚在椅上,微微側頭。這是他平時最喜歡的姿勢,沉穩又複雜的微笑也一如往常。
「我和海津信六不屬於同一個時代,這方面我不清楚。」這是他一開始的回答。
兩年前,佐田被派往波士頓和紐約的美術館見習半年。回國時,人們都說他舉止就像美國人,看了很不舒服。據說那次的美國見習,也是身居「局外」的佐田對主流派有種自卑感,總滿腹牢騷,當局為了安撫他,特地讓他到海外見習。
此時面對福原的提問,佐田像外國人一樣聳肩,一點都不足為奇。不過話說回來,佐田從美國歸來後宛如成了日本精神主義者。在一般雜誌上也常寫些帶這類色彩的雜文。有人不了解他這種傾向,但了解佐田的人則以洞察一切的口吻說──沒什麼,不過是一種生意手腕。這究竟什麼意思,似乎是個謎。佐田對海津信六退出學界的具體原因也只說一句「只能說是個謎」,答不出個所以然。
「像我說的,海津信六年輕時,活躍在山崎嚴明老師和垂水寬人老師那個時代。好久以前了。正值我們學生時代。我們無從得知內幕。」
面對這樣的回答,福原覺得佐田出奇謹慎,不像平時作風。
「可是應該有留下什麼傳說吧?」
「傳說是嗎?嗯,你問得好。嗯……」佐田沉聲低吟,眼角浮現魚尾紋,但皺紋大多被他的銀框眼鏡遮掩。「不過,也稱不上傳說吧。現在的年輕人連海津信六的名字也沒聽過。他不是名人,就當不成傳說。像我剛才說的,知道海津的價值、以他論文當自己論述基礎的全是現今那些教授。那件吸毒者殺人事件的報導刊在全國各大報上,恐怕上了年紀的學者看到海津信六的名字會大吃一驚,沒想他還活著,而且竟住在那種地方。」
又有一組人走進接待室,特別研究委員佐田趁這機會從椅子上起身。他和福原一起走向出口時,佐田像要混在其他聲音當中般悄聲對福原低語。
「雖然只是傳聞,不過,聽說海津信六落魄的原因,是女人。」
「女人?」
「這是傳說……詳情我也不清楚。」
佐田瘦削的臉頰浮現笑紋。
作者資料
松本清張(Matsumoto Seicho)
1909年生於北九州市小倉北區。因家境清寒,十四歲即自謀生計。 經歷過印刷工人等各式行業後,任職於《朝日新聞》九州分社。 1950年發表處女作〈西鄉紙幣〉一鳴驚人,並入圍直木獎。 1953年以〈某「小倉日記」傳〉摘下芥川獎桂冠,從此躍登文壇,開啟了專業 作家的生涯。 1957年於月刊上連載《點與線》,引起巨大迴響,開創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先河。 1992年逝世,享年八十二歲。 終其一生,以其旺盛的創作力,涵蓋小說、評傳、紀實文學、古代史、現代史等,作品數量驚人,堪稱昭和時代最後一位文學巨擘,亦是後輩作家景仰的一代宗師。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