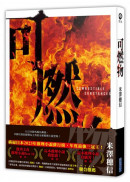內容簡介
◆已售出全球十四國語文版權!
◆入選「加拿大吉勒文學獎」最後決選!
◆榮獲加拿大最高文學榮譽「加拿大總督文學小說獎」!
◆當選2006年加拿大全國必讀書獎!
平凡真是夠了!到底誰能拯救我?耶穌基督或約翰藍儂?
二十一世紀終於有了經典小說!結合莎岡《日安憂鬱》的優雅敏銳與沙林傑《麥田捕手》的粗獷率直;你會希望這個故事永遠講下去……
這個夏天,諾蜜還要再失去什麼?
姊姊帶著媽媽整理的行李與祝福走了;媽媽忘了帶護照也在半夜走了。
「我問爸爸為何媽沒帶我走?老爸說:因為你還在睡。」
白白的雪地潑上豔紅雞血,形成美麗的潑墨畫。這是諾蜜對媽媽的記憶之一。
突然加速衝出路面的摩托車,被拋出的騎士維持坐姿騰空飛躍農田,是諾蜜對媽媽的另一個記憶。
「可以離開的人永遠都比不能離開的人酷,我是不能離開的人,因為老姊和老媽都已經離開了,而在這間空蕩蕩的屋子裡還有一個老男人,他除了我以外沒有別人……」
青春的苦悶說起來一點也不值錢,何況在信奉門諾教派的保守小鎮「東村」。
諾蜜比較想住在紐約那個自由又時髦的東村,跟搖滾樂手隨時到格林威治村閒晃。
舅舅說,在他的字典裡,「地獄」就緊接著排在「搖滾樂」後面。
鎮上的耶穌像穿件淺藍色長袍,兩手往外伸,手心朝上,好像在說,該死,我怎麼知道?我不過是個木匠罷了。
過完這個夏天,十六歲諾蜜即將高中畢業,會到「快樂家庭農場」剁雞頭。如果她按時交作業、上教堂做禮拜聽舅舅講道,不聽搖滾樂、不看「海角一樂園」電影……如果她沒有闖入柯里潘斯坦老奶奶的空屋,發現鎮上男人的祕密……諾蜜還有什麼沒失去呢?
加拿大新生代國寶級作家泰維茲化身十六歲少女,帶領你重溫青春的輕狂與苦澀,以充滿魅惑的文字,組織跳躍的意識,形成意象鮮明的圖畫,生猛有力地謳歌那說不完理不清的無邊苦悶!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我和我爸雷伊.尼克爾住在十二號公路旁那幢低矮的磚造平房裡。藍色百葉窗、棕門、一扇破損的窗子。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不過家具卻一直不見,使得情況變得很有趣。
我的家人不見了一半,我指的是比較漂亮的那一半。我和我爸早上起床,各忙各的,直到上床睡覺。每天晚上十點左右,我爸都會告訴我說他要去睡了。回他臥室的路上,他會在玄關停下,把便利貼黏在鞋尖上,提醒自己第二天待辦的事。我們很喜歡一起觀看北極光。我把齊林老師在課堂上教的一字不漏地告訴我爸,說北極光是怎麼形成的。他認為齊林老師的見解有點意思。他對齊林老師的見解總是興趣不大,可能因為他自己也是老師的緣故吧。
我有作業得做完。就是這個詞,「做完」。對於「把事情做完」這件事,我一直都有點問題。齊林老師跟我說,文章和故事都會有系統地走到作者無法控制的預定結尾。他說結尾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了。我倒不知道這些個,我覺得結尾可以有很多,就從中挑選嘍。我已經在期盼失敗的到來,這件事我學得可多了。可是,這些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當我住在一個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一座小鎮邊緣、一家光線黯淡的爐渣磚造屠宰場裡、弄斷細細瘦瘦的脖子、再把帶著羽毛的屍身丟到輸送帶去!附近年輕人最後多半都到「快樂家庭農場」工作,這裡是本地雞隻們去見牠們造物主的好地方。我今年十六歲,馬上要從高中畢業,再過幾個月,就要在這條死亡裝配線上就定位。
對我媽楚蒂.尼克爾,我那些一再出現的回憶就有個和殺雞有關的。我和她站在這個農場院子裡,看著卡森和他爸砍斷一隻隻雞的頭。你看到卡森就會認得。卡森.恩斯,坐後排的「手臂屁聲王」、「變態社社長」。他說他在南邊的潘西小鎮有個私生子。卡森是個問題兒童,不過如果你知道他以前曾經是「雪衣殺手」的話,這就沒啥了不起了。當時我八歲,我媽大概是三十五歲,她穿著一件紅色毛線外套,還套了雙雪靴。她頭髮髮尾全都給凍住了,因為那天早上她找不到吹風機。你看,她這麼說。然後抓住一綹頭髮,把它像一根草一樣地折彎了。她把她那條變形蟲圖案的領巾給我綁成頭巾。我不太清楚我們到卡森家身歷那種殘殺場面要幹嘛,我很確定剛開始時並非那樣,不過我想殘殺總是有辦法偷偷逼近你。卡森跟我同年,每當他要揮斧頭,他都會對雞隻喊話,要雞快逃。快跑,你這隻笨雞!卡森,他爸就會說。他只喊他名字,頭再微微欠扁地搖了搖。他盡一切力量要把兒子養成一個殺手。那是冬日下午四點半左右,天色逐漸暗成藍藍的,天空橫向飄著雪,我們全都站在一盞巨大的黃色街燈下。哦,我們當中有一些正要送命呢。卡森笨手笨腳地做著這個活兒,用毫不正確的方式砍雞脖子,還一邊小聲指示雞隻逃命。快飛走呀,白癡。別逼我這麼做,可憐的孩子。這時候他已經把雪衣上半身的拉鍊拉開,所以鬆垂的上衣像裙子般垂在腰間,延緩了他的動作。他爸看到就走過來,從卡森那戴著露指手套的小手裡把砍了一半的雞抓過來,摔放在雞隻的木頭祭壇上,再用無比快速又精準的手法把頭砍下,不到一秒鐘就在雪地上創作出一幅潑墨畫。鮮血怎能如此快速又無聲無息地灑在地上把我給嚇呆了。我媽倒抽一口氣說,你看,諾蜜,這是波拉克的抽象畫呢。哦,好美呀。哦,她說,這是天國的畫布呢!她經常這樣說。我和卡森站在那裡,盯著雪上的血。我媽說,就這樣?誰曉得會這麼容易。
我不知道她是說創作藝術很容易呢,或是殺雞很容易,還是死亡很容易?這些事情當中的每一件,在我看來都很不容易。我想像如果此時此刻她就在這裡,我問她那時候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她將會說,你問的是什麼事啊?而我會說,哦,沒事。然後到此為止。
只因為她走了,所以那些過去的瑣事才會一再重現。當天,在卡森家看殺雞之後,晚餐時她問我們,如果因為某種原因我們全都陷入昏迷,睡過了夏天,直到十一月中才醒來,我們會生氣自己錯過了夏天的溫暖和美麗呢,或是開心我們好歹還活著?不喜歡做選擇的老爸問她,我們可不可以兩者都有,她說不可以。她覺得不行。
我媽不在這裡了。在我姊泰雪離開後不久,她也離開了。我和我爸都不知道她們任何一個的下落。只知道泰雪是跟齊林老師的姪子艾恩一起走的。艾恩會軟骨功,還有一輛福特「爬山虎」貨車。我媽似乎是自己一個人走的。
好,說說我爸吧。你知道在那些漫長的夜晚,我們坐在那個12號公路旁的家裡,我爸說些什麼嗎?他說,嘿,諾蜜,來轉唱盤怎麼樣?沒錯,他就專愛講這種讓人受不了的話。那表示他想再聽聽安瑪利唱「雪鳥」,或是我那張泰瑞傑克斯四十五轉舊唱片的「陽光季節」──九歲那年,也就是我真正意識到自己存在的那一年,我經常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放著這首歌,超樂的。我們很開心。近來老爸常把「胃」這個字當動詞用,還有「團結」也是。我們團結我們胃。我指出這事兒,他還否認。他說我們過得很開心,也撐下去了。也是啦,他爲什麼不能否認?他告訴我說生命充滿了承諾,不過我猜想他指的是保證結束的承諾,因為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出任何其他種類的承諾。如果我們能離開這個鎮,或許會好一點,但是我們離不開,因為我們在等我媽和我姊回來。已經三年了。我的初經在我媽離家的第二天來潮,這表示從她們走了以後,我已經流了三十六次血。
這個鎮超嚴肅又亂安靜的;簡直要把我逼瘋。我常想會不會有人因為這種安靜而悶死。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對我們的言語施加穩定的壓力,像有一隻手對著裂開流血的傷口一直用力。鎮公所裡面有一個好大好大的檔案櫃裡面裝著死亡證明書,當事人不是被自己氣死,就是鬱悶以終。「靜默之音」。夜裡你聽得到的聲音只有半拖車疾駛過公路,車裡載著被下藥的動物,要去挨刀子。可別跟這些牛隻對看。這裡的人似乎等不及要去死,死亡是最重要的大事。我們沒在出生時全給掐死,唯一的理由是那樣就不能讓我們受一輩子的苦。我的輔導諮商老師曾建議我要改變對這裡的態度,要學著去愛這裡。可是我有做呀,我告訴她。哦,那倒新鮮了,她說。那倒新鮮了。
我們是門諾派教徒。據我所知,這是青少年所屬的次級教派中最讓人尷尬的一種。五百年前,歐洲有個叫門諾.西蒙斯的人創立了這個奇怪的宗教,他和追隨者在荷蘭、波蘭、俄國到處被打被殺,要不就被逼要改信當地的宗教,直到他們,至少當中一些人,終於到了我現在坐著的這個地方。諷刺的是,他們給這裡取名「東村」,而這可是紐約市一個我最希望去住的地區的名字耶。還有一些其他人跑到巴拉圭,一個叫「廈谷」的巨大灰土谷地,那裡是全世界最熱的地方。我朋友麗蒂雅就是從巴拉圭搬到這裡的,她跟我講了很多因為天氣熱而引起的瘋狂故事。她有個叔叔,經常坐在村子廣場上一個倒放的飼料桶上,尖叫著要人把他的腦子還給他。要到夜裡涼爽時才能稍微跟他正常地說話。我們應該是歡歡喜喜地渴望死亡,而在那個幸運的日子(那叫做「被提」)到來以前,我們的生活就該是死亡的樣本,或者至少是死亡過程的模擬。
門諾教派的電話訪查可能會有這類問題:你喜歡活著或是願意慘死?如果你回答「活著」,那個訪查的門諾教徒就會掛你電話。對了,你就想像一下嘍,假設你學校裡有格最不能適應的同學,他自己去組了個社團,這個社團的宣言包括:禁止接觸媒體、跳舞、抽菸、溫和的氣候、電影、喝酒、搖滾樂、為玩樂而做愛、游泳、化妝、首飾、撞球、進城或過九點還不睡覺……這就是百分之百的門諾教徒了。真是太多謝了,門諾.西蒙斯。 有個人竟然認為用他自己的名字來涵蓋統稱一群人是種謙卑的行為,你對這個人應該也會有點火大吧,而且還是用他的名字,還不是姓氏哦。「諾蜜教派」你覺得怎麼樣?嗯。也許我在殺雞場待段時間,也要開始來組織一群人。有時候我會想像門諾.西蒙斯是州際公路旁一家位在美麗林區的療養院裡的妄想症病患,拖著腳步走去接受團體治療,或是把他的藥偷藏幾顆起來。我怎麼會跑進這個男人夢想創造出的可怕壁畫之中呢?這個想法令我十分不安。我常猜想門諾.西蒙斯的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他遺世遠走?我不知道如果門諾.西蒙斯童年「典型的一天」如果重現,會是什麼樣子?我聽過托爾金和蛾蘇拉.勒.昆恩還有寫《瓦特希普高原》關於兔子有趣寓言的那個傢伙,不過我可不是什麼幻想小說迷,因為這裡每天已經有太多幻想,不停地硬塞到我們肚子裡。「獸印」?「街道是精金」?「七匹白馬」?什麼?去他的!我的夢想是逃往「真實」世界。如果強迫我再看一本「納尼亞」系列,我就去死!我還寧願看一本和我同年的女孩寫的日記哩──一個城市少女的日記之類的,或是一本都市計畫的教科書,再不然一本紐約市的電話簿也行。如果能有一本紐約市電話簿,要我殺人都可以。
我媽總說她的眼睛是榛子般的淡褐色,不過其實和我爸的煙青色沒兩樣。我爸和我媽是遠房表親,所以我和泰雪不只是姊妹,也是遠房表姊妹。鎮上的遺傳基因沒什麼深奧之處,這聽起來像個老掉牙的笑話,但對我們來說卻一點也不好笑。不是,媽說,是淡褐色的,我的護照上都註明是淡褐色,你再看仔細點。我和泰雪看了看,沒看到像是榛子的東西,沒有斑點、沒有線條,不過我們說,好吧,是榛子色。很好。你要護照做什麼?我姊問。我媽說用來證明身分啊。我想她認為有本護照就可以找一天搭上飛機、飛到一個有暖和天氣、居民可以跳舞的神奇地方。這讓她有種冒險的感覺吧。
我們不鼓勵門諾教徒去四十哩外的城市,但卻鼓勵他們帶著大批「基甸協會」贈送的聖經和髮網前往最最偏遠的第三世界國家。也許我媽現在就在那裡:在剛果蓋教堂,身穿漂亮的花布長裙、橡膠雨鞋,還戴頂草帽。不過我懷疑。這是「嘴巴」要那些可能是「拉子」但卻被稱做老處女的單身老女人做的事:給她們一把鏟子、每個月若干零用錢和一架相機,派她們出去,好讓她們每幾年才回來一次,在教堂地下室舉行幻燈片欣賞會,給所有的小門諾教徒看。幻燈片結束時,村落裡最火爆的傢伙總是會改變信仰,開始穿上普通衣服、不顧族人的威脅和不以為然,幫助這些白人女同志從事她們的善行。有時候傳教士會遇害,不過這種事也無可奈何。在這些幻燈片裡,通常都會有一個奇怪的、逐漸會爆發的次要情節,不是把巫醫趕出城鎮,就是要他對鏡頭微笑,同時拿起一本《新約聖經》,這就表示,讚美主,他得救了。幻燈片結束後,我們會吃乳酪和小圓麵包,也許還在大廳玩一下捉迷藏。
總之,我無法想像我媽變成傳教士的模樣。我倒可以想見她做別的事情,例如深海潛水或在歐洲帶觀光團。楚蒂是葛楚德的簡稱,當她知道美國作家葛楚德.史坦和她在巴黎那些貓的故事後,她就比較不那麼討厭自己的名字了。她一直想要去看看巴黎。她會用濃濃的法國腔唱賈克布瑞爾的老歌;她誇張搞笑地大聲唱。不過泰雪告訴我說那只是「假象」,她說我媽被沒完沒了的家事操勞到已經整個昏頭了,還說她遭受父權體制的壓迫。
我媽愛看書,不過多半看懸疑小說(雖然我們這裡最愛說世界上沒有懸疑神祕這種事)或是二次大戰猶太人受到的浩劫。她喜歡說「不真實」這幾個字。這太不真實了。她會這麼形容那些讓她驚異或失望的事,而似乎這樣的事情還挺多的。她也喜歡很有興味地說「呼咦」,這是針對任何能讓她興奮的小事的反應。例如全家人坐在馬達小船裡遇上大浪、全家人把車打空檔滑下山坡、全家人砍下一棵聖誕樹。我們全家。還有一個她常說的話,那是當在她看書而不想回答我們去打擾她的任何問題時,就是「什─麼─呀」。一個拖得好長好長的句子,聲音從低到高到持續的高;她的眼光卻不離開書本。嘿,媽,我要到外面把汽油倒在身上然後劃根火柴。什─麼─呀?眼睛還是絕不離開書本。我還真愛死她這樣呢。
我媽的夢想是去聖城耶路撒冷。她對猶太人充滿好奇,我們鎮上一個猶太人也沒有,也沒有黑人或亞洲人。我們看起來全都很像,簡直就像置身科幻小說的世界。我和我姊早上去上學,我媽穿睡袍站在門口說再見,再見,我愛你們,祝好運,好好玩,一直到我們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為止,好像我們是外國水手,共度過極不真實的奇妙一晚後,即將離開港口。等我們下午四點回家,她還是穿著睡袍,不過這時她窩在沙發裡,一根手指頭放在書中當書籤,說哈囉,哈囉,你們這一天過得怎樣?可別告訴我現在已經過四點了。是過四點了,我們說。有什麼可以吃的?我媽就會很快坐起來,而通常接著就會說,哦,我坐起來太快了,於是我們就得等個五秒鐘,等她把頭腦弄清楚些。她穿著一雙幾乎是圓球形的豔紅羽絨拖鞋。一小時之內,她會穿好衣服去雜貨店「男人婆」(是誰給雜貨店取這種性別特例的名字?)買回晚餐食材、做好晚餐、放在餐桌上,笑吟吟,開心、親切、毫無煩惱。
她是「客里客」高手;「客里客」是種肉罐頭,那些肉看起來很像壓碎的人肉,罐頭上附個小鑰匙,可以沿著罐頭扭開罐蓋。我希望能有些關於她的更鮮明的事實,具有高解析度色調鮮明的完整圖像,但她很難讓人簡單詳細地描述清楚。
她內心有某種東西翻攪著,是種狂猛無法預料的東西,好像藏在生日蛋糕裡的一把鋸子。她扮演一個心滿意足的角色,就像傑克尼可遜在電影「飛越杜鵑窩」裡假扮瘋子一樣。不過我爸倒眞的心滿意足穿西裝打領帶坐在餐桌首位,和他兩個相對而言算正常的女兒和喜愛歡樂的妻子開著玩笑,這個妻子有榛子色的雙眼和性感睡衣,還有放在梳妝台最上層抽屜裡的一本護照,護照上有一張充滿魅力的黑白照片。
我媽最常出遊的地方是教堂地下室。鎮上的婦道人家都必須在那裡待很長的時間,不去就會下地獄(你要服侍誰?是波札那的傳教士還是撒但?對啦。沒問題吧?我想也是)。她們的工作是爲傳教士縫衣服和被毯,並且裝箱運送到海外。我媽討厭這件事。她曾經把幾本羅曼史小說丟進要寄到尼加拉瓜的箱裡而惹了麻煩。她應該要去教會做各種事,替婚喪儀式燒菜、縫被子、教主日學,以及加入那些謙卑助人的團體。她們總是在打電話,問她能不能騰出一些時間來幫忙?其實根本不是真的在徵詢你同意。有時候她會在最後一刻才去,嘴裡說,哦,我應該去了,我馬上就去。
即使她哥是超級鎮長也沒用,這就好像你是格達費或史達林的妹妹一樣。你不跟人同一陣線,就要完蛋。我爸喜歡她去幫忙,可是她不去幫忙,他也喜歡。似乎他永遠也弄不清自己最愛的是哪一個楚蒂,是穿著雪靴在教堂地下室幫忙的那位溫婉的女士,還是穿著性感內衣的叛逆小妞?我想這兩個極端都只是我媽擺出來的樣子,真正的楚蒂介於兩者之間。不過這個鎮就是這樣──沒有中間地帶。你不是在裡面就是在外頭。不是好就是壞──其實是非常非常好和非常非常壞。再不就是把非常壞做得非常好,而不讓人發現。
延伸內容
花兒,你要到哪裏去 ◎文/周芬伶
在信與非信,善與非善之間,可有模糊地帶?住在十二號公路旁的女孩,要告訴你游離於模糊地帶的感受。
好讀耐讀的筆調,迴盪在山谷的清音,是繼馬格麗特愛伍得、愛莉絲孟若之後值得期待的新世代作家。
這部小說原文的直譯為《複雜的善意》(A Complicated Kindness),本書的譯名較平易近人,但千萬別以為這只是本公路小說或成長小說。它可說是以回憶筆調描寫的心靈故事;少女心靈故事像莫里森的《藍眼珠白皮膚》或莒哈絲《情人》,她們除了充滿抒情化的傾訴,詩意的筆調,核心事件看來是愛情,但它只是表層,在其下湧動的是親情衝突、文化與膚色界限,而這本書卻是人與信仰或信念之間的戰爭。可見作者的企圖心之強烈,用溫情包裝強烈的質疑與叛逆,以小女孩無畏的眼光挑戰各種理念。
主角諾蜜,是一個生於長於東村(East Village)的十六歲女孩。她擁有正常的少女的慾望與夢想,愛聽搖滾、也愛嬉皮青年、更愛她那充滿叛逆精神的姐姐泰雪,以及熱情傻氣的母親,但對於生活在僵化教條中的東村居民,她是個離經叛道,幾乎被視為瘋癲的邊緣人。尤其在姐姐離去,母親失蹤,男友也遠走高飛,諾蜜的行為越來越脫軌,思緒越來越狂亂,她周圍的人對她的敵意,家中的傢俱一個個消失,整個家一步步走向瓦解,她一邊想念母親與姐姐,一邊與男友幻想著到遠方去,直至也被宣判「逐出教會」。
小說可說是由 諾蜜的幻想和傾訴構成,像書信或回憶錄。她內心是個敏銳,細膩,善良的孩子;在失去所愛的傷痛後,才用反叛,泠淡,和嘲諷來對抗身邊不近人情的世界。諾蜜的夢想,是有朝一日能離開死寂的東村,到紐約過她嚮往的自由生活。在她的想像中,外面是個廣闊的繁華世界,逃避者的天堂。
她的姐姐因為吸毒與總總放縱行為被驅逐,這不令我們感到意外,但連她那充滿愛心與服務熱誠的母親也被驅逐,這讓諾蜜的家庭破裂,她的心靈也陷入分裂中,她的自語有時溫馨甜美,有時激烈混亂,因為她的價值系統崩潰的,分不清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她把自己說得很壞很壞,因為所有的審判都來自「嘴巴」,也就是她的舅舅,他是無所不在的監督者。諾蜜抵擋的方法是疏離與逃避,外在的打擊越猛烈,回憶就越溫馨童真,當最後的懲罰來臨,她的行為與心靈退化至幼童狀態,令我們動容。
時代改變了,新的事物不斷滲透進來,被認為邪惡的電視與搖滾樂、性享樂、大麻……,讓許多人無所適從,與其說他們「叛教」,不如說是「迷失」或「分裂」,諾蜜可說是東村人的縮影,她只要一個完整的「家」,一份踏實的「愛」,或是青春放浪,但在東村到處是破碎的家庭,或心破了洞的人,他們被「迴避」,或者被「驅逐」。通姦的婦人、嗑藥的青年、無神主義者、叛教者……,只要一不小心就會觸犯教規。
信仰應來自內部,而非外部。
書中常提到的西蒙斯,是門諾教派的引領者,他本是一名荷蘭天主教神父其後轉換為Anabaptist信仰,為新教團體的後裔,在1524年,門諾西蒙斯的立場逐漸轉變為激進。門諾教派拒絕嬰兒的洗禮,宣誓就職的宣誓,兵役,和世俗性。 他們實行強有力的教會紀律,信奉生活的簡單,誠實,熱愛生命,都在仿真最早的基督徒。門諾派的神學原則,強調直接的影響,聖靈對著心靈的溝通,其中最重要的是聖經,從救恩的信息透過神秘經驗感受基督的存在。
但那只是表象,作者揭開門諾神秘的面紗,這是這本書有議題性的所在,當帶領者的魅力失去,宣教者的教條已成枷鎖,對嬉皮世代而言更是水火不容,生長在相同背景的作者,深切地體會與告白,諾蜜的獨白看似稚弱,其實她在價值混亂中,一直在尋求出口,卻到處碰壁,親情、愛情、友情……,在一一破滅之後,她一無所有,相對的也獲得自由,代價跟殉道一樣巨大。
如果對小說的這些背景無深入瞭解,讀者可能會只把本書誤讀為叛逆少女的逃避故事,一個成長小說。但小說人物居住的東村,正是門諾教徒的村落,他們保持古老基督門徒的神聖傳統,而成為神秘令人好奇的村落,裏面還建立民俗村供人瞻仰,在街的另一頭是殺雞工廠,小孩長到十幾歲便被送去那裏工作。但在外人的眼中,他們跟期望不符:
進到我們「真實」小鎮的美國人,不是驚訝就是失望,或者兩樣心情都有。他們看到我們有些人坐在路邊抽菸,身穿小可愛,他們可真是亂不高興的,花了不少錢才到這裏來,就是要看頭戴軟兜帽的、身穿圍裙的,還有騎馬車的才對啊。
有一次有個觀光客走過來,給我拍了一張照,並且對她丈夫,這可是一種無價的新舊兼容並蓄呢。他們為了要不要給我一些錢而爭執了一番。
我可是會說英語的哦,我說。我們的主要產業是人造民俗村和馬路以及再過去幾哩路的雞隻屠宰場。在炎熱的夜裏,如果風向對了,雞血和雞毛的味道會送我們上床,像壞心的母親一樣這裏沒有鐵窗或是看得見的出口。
宗教上的僵化教條也許令人覺得不適,但最令諾蜜覺得憤怒與諷刺的,大概就是整個社群正在將那種帶給自己痛苦的生活,包裝成一種歡愉的商品,向外來的觀光客兜售,這種偽善幾乎要叫人尖叫。信仰上的倚靠已然幻滅,她仍需要捉住某種毋需涉及神的信念,好讓自己不至於被虛無沖垮,橫跨六七零年代的嬉皮運動所蛻變出的波希米亞式的放浪生活與龐克的反叛精神,似乎是個出口,前者傳授的是種關於躲避與流浪的藝術,後者教導人要永遠站在這個世界的對立面,要反抗一切!且戰且走,躲避與反抗就是諾蜜為她的生命,所暫時找到的游擊隊路線,外表陰美,行為激烈的Lou Reed曾是她的神。
但那個年代對某些過來人來說,是由夢轉痛的心路歷程,身為一個小說家要選擇從何處切入那個時代,是一大問題。這本書採取從一個門諾小鎮的女性青少年的視點來進入六七零年代,這種安排相對來講倒是奇特,但它也與作者不尋常的生平吻合。因此在整本小說之中,瀰漫著一股屬於花兒世代凋謝後,特有的失落氛圍,比戰後文學那種純粹的絕望多了點什麼,但解脫之道可能不再只是天真的希望,單純的善良。
這引領我們回到這本小說的主題:複雜的善意。
從教會生活到嬉皮甚或龐克文化,我們相信提倡這些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人都是帶著善意的,為何這些不同的善意都會被理解成是複雜的?
也許是因為它可能潛意識裡包藏著惡意,或過於拘泥於某些條件與目的,也可能是它在不斷的傳播中漸漸變質。西方人相信到地獄的道路是以善意鋪成的,有種說法叫做「善意的謊言」,但有時候是否善意本身就是某一種形式的謊言?
本書暗地裡審視了每一種在諾蜜的成長中,曾經參與過的謊言,無論那個謊言是來自於教會、家庭、友誼、愛情、性冒險、搖滾樂、毒品或嬉皮生活,都在在為那個時代的參與者,還有諾蜜提供一份善意的抉擇。但在成長與衝突的過程中,諾蜜不斷感受到這種埋藏在善意之中的謊言成份,不誠實成份,阻止著她去認識真實與自我,最壞的還是自己騙自己,天真的相信答案只存在他方,他人身上。她感到一種自身不能見容於的雜質、異物感,但沒有《麥田捕手》裡那般無因由的憤怒,她只是有點暈眩與困惑。
有人把作者與沙林傑和沙岡相比,我覺得跟《麥田捕手》不同的是,作者的寫法較熱;然她又比沙岡來的溫馨,叛逆的性質差異很大,這三者很難相提並論,但又不能歸類為宗教小說,只能說夾在宗教小說與成長小說之間,兩者拉扯產生的猶疑與曖昧。我覺得所有描寫信仰、信念甚或改宗的作家,應該都需要探討到反叛,與重拾虔信或尋道之艱難。這本小說的作者尚且年輕,已把第一階段寫得很有火侯,後續也值得期待,令我們想起艾莉斯孟若柔弱與隱微的筆調。但孟若專攻短篇,長篇的女性小說家就以Miriam Toews是新起之星,令人好奇作者的寫作動機與成長歷程。
生於1964年的 Miriam Toews出生於斯坦貝奇,馬尼托巴MENNONITE鎮。 她在被隔絕的,保守的宗教社區成長經歷種種價值衝突,以及搖擺不安的年代,這提供她對家庭生活的細膩描寫與觀察。 Toews的第一本小說《我的幸運之夏》,表現了她令人驚喜的幽默和尖銳筆調。 主角是兩個單親母親的故事,描寫在一個低收入住房建造計劃中,如何逃避母親的死亡以及引發的精神創傷,她的文字清新而無陳腔濫調。 Toews的第二部小說《好男孩》描寫一個單親母親和缺席父親歸鄉的故事,表現作者柔和的諷刺技巧,常引起讀者同情她筆下的人物。
作者關懷現代家庭面臨的種種沖刷,以及女性的困境,頗能引起廣大的共鳴。她柔和的筆觸具有滲透力,柔和是她的優點,但年齡與特殊的生平卻絕對是她最大的本錢,看來這位的五年級女性作家正在創作的高點,還年輕還令人期待。
總之,這是一本青春之書,也是叛逆之書,是你我都經歷但想也想不清楚,說也說不明白之事,卻是書寫不盡之事,年少的心像風吹過草原,誰能補捉?
在信與非信,善與非善之間,可有模糊地帶?住在十二號公路旁的女孩,要告訴你游離於模糊地帶的感受。
好讀耐讀的筆調,迴盪在山谷的清音,是繼馬格麗特愛伍得、愛莉絲孟若之後值得期待的新世代作家。
這部小說原文的直譯為《複雜的善意》(A Complicated Kindness),本書的譯名較平易近人,但千萬別以為這只是本公路小說或成長小說。它可說是以回憶筆調描寫的心靈故事;少女心靈故事像莫里森的《藍眼珠白皮膚》或莒哈絲《情人》,她們除了充滿抒情化的傾訴,詩意的筆調,核心事件看來是愛情,但它只是表層,在其下湧動的是親情衝突、文化與膚色界限,而這本書卻是人與信仰或信念之間的戰爭。可見作者的企圖心之強烈,用溫情包裝強烈的質疑與叛逆,以小女孩無畏的眼光挑戰各種理念。
主角諾蜜,是一個生於長於東村(East Village)的十六歲女孩。她擁有正常的少女的慾望與夢想,愛聽搖滾、也愛嬉皮青年、更愛她那充滿叛逆精神的姐姐泰雪,以及熱情傻氣的母親,但對於生活在僵化教條中的東村居民,她是個離經叛道,幾乎被視為瘋癲的邊緣人。尤其在姐姐離去,母親失蹤,男友也遠走高飛,諾蜜的行為越來越脫軌,思緒越來越狂亂,她周圍的人對她的敵意,家中的傢俱一個個消失,整個家一步步走向瓦解,她一邊想念母親與姐姐,一邊與男友幻想著到遠方去,直至也被宣判「逐出教會」。
小說可說是由 諾蜜的幻想和傾訴構成,像書信或回憶錄。她內心是個敏銳,細膩,善良的孩子;在失去所愛的傷痛後,才用反叛,泠淡,和嘲諷來對抗身邊不近人情的世界。諾蜜的夢想,是有朝一日能離開死寂的東村,到紐約過她嚮往的自由生活。在她的想像中,外面是個廣闊的繁華世界,逃避者的天堂。
她的姐姐因為吸毒與總總放縱行為被驅逐,這不令我們感到意外,但連她那充滿愛心與服務熱誠的母親也被驅逐,這讓諾蜜的家庭破裂,她的心靈也陷入分裂中,她的自語有時溫馨甜美,有時激烈混亂,因為她的價值系統崩潰的,分不清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她把自己說得很壞很壞,因為所有的審判都來自「嘴巴」,也就是她的舅舅,他是無所不在的監督者。諾蜜抵擋的方法是疏離與逃避,外在的打擊越猛烈,回憶就越溫馨童真,當最後的懲罰來臨,她的行為與心靈退化至幼童狀態,令我們動容。
時代改變了,新的事物不斷滲透進來,被認為邪惡的電視與搖滾樂、性享樂、大麻……,讓許多人無所適從,與其說他們「叛教」,不如說是「迷失」或「分裂」,諾蜜可說是東村人的縮影,她只要一個完整的「家」,一份踏實的「愛」,或是青春放浪,但在東村到處是破碎的家庭,或心破了洞的人,他們被「迴避」,或者被「驅逐」。通姦的婦人、嗑藥的青年、無神主義者、叛教者……,只要一不小心就會觸犯教規。
信仰應來自內部,而非外部。
書中常提到的西蒙斯,是門諾教派的引領者,他本是一名荷蘭天主教神父其後轉換為Anabaptist信仰,為新教團體的後裔,在1524年,門諾西蒙斯的立場逐漸轉變為激進。門諾教派拒絕嬰兒的洗禮,宣誓就職的宣誓,兵役,和世俗性。 他們實行強有力的教會紀律,信奉生活的簡單,誠實,熱愛生命,都在仿真最早的基督徒。門諾派的神學原則,強調直接的影響,聖靈對著心靈的溝通,其中最重要的是聖經,從救恩的信息透過神秘經驗感受基督的存在。
但那只是表象,作者揭開門諾神秘的面紗,這是這本書有議題性的所在,當帶領者的魅力失去,宣教者的教條已成枷鎖,對嬉皮世代而言更是水火不容,生長在相同背景的作者,深切地體會與告白,諾蜜的獨白看似稚弱,其實她在價值混亂中,一直在尋求出口,卻到處碰壁,親情、愛情、友情……,在一一破滅之後,她一無所有,相對的也獲得自由,代價跟殉道一樣巨大。
如果對小說的這些背景無深入瞭解,讀者可能會只把本書誤讀為叛逆少女的逃避故事,一個成長小說。但小說人物居住的東村,正是門諾教徒的村落,他們保持古老基督門徒的神聖傳統,而成為神秘令人好奇的村落,裏面還建立民俗村供人瞻仰,在街的另一頭是殺雞工廠,小孩長到十幾歲便被送去那裏工作。但在外人的眼中,他們跟期望不符:
進到我們「真實」小鎮的美國人,不是驚訝就是失望,或者兩樣心情都有。他們看到我們有些人坐在路邊抽菸,身穿小可愛,他們可真是亂不高興的,花了不少錢才到這裏來,就是要看頭戴軟兜帽的、身穿圍裙的,還有騎馬車的才對啊。
有一次有個觀光客走過來,給我拍了一張照,並且對她丈夫,這可是一種無價的新舊兼容並蓄呢。他們為了要不要給我一些錢而爭執了一番。
我可是會說英語的哦,我說。我們的主要產業是人造民俗村和馬路以及再過去幾哩路的雞隻屠宰場。在炎熱的夜裏,如果風向對了,雞血和雞毛的味道會送我們上床,像壞心的母親一樣這裏沒有鐵窗或是看得見的出口。
宗教上的僵化教條也許令人覺得不適,但最令諾蜜覺得憤怒與諷刺的,大概就是整個社群正在將那種帶給自己痛苦的生活,包裝成一種歡愉的商品,向外來的觀光客兜售,這種偽善幾乎要叫人尖叫。信仰上的倚靠已然幻滅,她仍需要捉住某種毋需涉及神的信念,好讓自己不至於被虛無沖垮,橫跨六七零年代的嬉皮運動所蛻變出的波希米亞式的放浪生活與龐克的反叛精神,似乎是個出口,前者傳授的是種關於躲避與流浪的藝術,後者教導人要永遠站在這個世界的對立面,要反抗一切!且戰且走,躲避與反抗就是諾蜜為她的生命,所暫時找到的游擊隊路線,外表陰美,行為激烈的Lou Reed曾是她的神。
但那個年代對某些過來人來說,是由夢轉痛的心路歷程,身為一個小說家要選擇從何處切入那個時代,是一大問題。這本書採取從一個門諾小鎮的女性青少年的視點來進入六七零年代,這種安排相對來講倒是奇特,但它也與作者不尋常的生平吻合。因此在整本小說之中,瀰漫著一股屬於花兒世代凋謝後,特有的失落氛圍,比戰後文學那種純粹的絕望多了點什麼,但解脫之道可能不再只是天真的希望,單純的善良。
這引領我們回到這本小說的主題:複雜的善意。
從教會生活到嬉皮甚或龐克文化,我們相信提倡這些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人都是帶著善意的,為何這些不同的善意都會被理解成是複雜的?
也許是因為它可能潛意識裡包藏著惡意,或過於拘泥於某些條件與目的,也可能是它在不斷的傳播中漸漸變質。西方人相信到地獄的道路是以善意鋪成的,有種說法叫做「善意的謊言」,但有時候是否善意本身就是某一種形式的謊言?
本書暗地裡審視了每一種在諾蜜的成長中,曾經參與過的謊言,無論那個謊言是來自於教會、家庭、友誼、愛情、性冒險、搖滾樂、毒品或嬉皮生活,都在在為那個時代的參與者,還有諾蜜提供一份善意的抉擇。但在成長與衝突的過程中,諾蜜不斷感受到這種埋藏在善意之中的謊言成份,不誠實成份,阻止著她去認識真實與自我,最壞的還是自己騙自己,天真的相信答案只存在他方,他人身上。她感到一種自身不能見容於的雜質、異物感,但沒有《麥田捕手》裡那般無因由的憤怒,她只是有點暈眩與困惑。
有人把作者與沙林傑和沙岡相比,我覺得跟《麥田捕手》不同的是,作者的寫法較熱;然她又比沙岡來的溫馨,叛逆的性質差異很大,這三者很難相提並論,但又不能歸類為宗教小說,只能說夾在宗教小說與成長小說之間,兩者拉扯產生的猶疑與曖昧。我覺得所有描寫信仰、信念甚或改宗的作家,應該都需要探討到反叛,與重拾虔信或尋道之艱難。這本小說的作者尚且年輕,已把第一階段寫得很有火侯,後續也值得期待,令我們想起艾莉斯孟若柔弱與隱微的筆調。但孟若專攻短篇,長篇的女性小說家就以Miriam Toews是新起之星,令人好奇作者的寫作動機與成長歷程。
生於1964年的 Miriam Toews出生於斯坦貝奇,馬尼托巴MENNONITE鎮。 她在被隔絕的,保守的宗教社區成長經歷種種價值衝突,以及搖擺不安的年代,這提供她對家庭生活的細膩描寫與觀察。 Toews的第一本小說《我的幸運之夏》,表現了她令人驚喜的幽默和尖銳筆調。 主角是兩個單親母親的故事,描寫在一個低收入住房建造計劃中,如何逃避母親的死亡以及引發的精神創傷,她的文字清新而無陳腔濫調。 Toews的第二部小說《好男孩》描寫一個單親母親和缺席父親歸鄉的故事,表現作者柔和的諷刺技巧,常引起讀者同情她筆下的人物。
作者關懷現代家庭面臨的種種沖刷,以及女性的困境,頗能引起廣大的共鳴。她柔和的筆觸具有滲透力,柔和是她的優點,但年齡與特殊的生平卻絕對是她最大的本錢,看來這位的五年級女性作家正在創作的高點,還年輕還令人期待。
總之,這是一本青春之書,也是叛逆之書,是你我都經歷但想也想不清楚,說也說不明白之事,卻是書寫不盡之事,年少的心像風吹過草原,誰能補捉?
悲傷、愚蠢、卻又充滿希望,這就是青春之所以美好的原因吧!
◎文/Joanna & 王若琳
Reading this book, and the thoughts of our protagonist, Nomi, I can't help but be reminded of the dialogues and jokes I held with my sisters and friend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Sarcastic, self-deprecating, silly, and just overall teenage. (I'd like to think that's a permanent phase for me that I'll never "grow out of." Although I really wouldn't call it that, it's more like "lose" your teenage rather than grow of out it.) There are times when, reading this book, I was really reminded of my highschool life; how everything was felt so fiercely, and that was for things both bitter and wonderful. I remember how fiercely I felt about this boy named Nathaniel in high school. Sometimes, we would sit in his car at night and talk about deep and profound things that are probably now laughable, we kissed and when I saw him flirt with other girls I would always dramatically wander off, either crying or just angry. But that was the beauty of teenage. Everything was so very sad, stupid, angry but hopeful. I just wanted to be free and experience all that I could. Be an artistic person, be a smart person, be somebody cool, but how? Still trying to figure that out.
讀著這本書,及主角諾密的種種想法時,我不由自主地被拉回到中學時期和姊妹、朋友間的對話與玩笑,以及那段挖苦、自貶、糊里糊塗的年少時光(我想對我來說那是個從未「因長大而遺棄」的永恆階段,雖然不想這麼說,但其實我們比較像「失去」年少,而非「因長大而遺棄」)。讀這本書時,確確實實的讓我會回想起我的中學生活,每件事物都感受都如此的強烈、鮮明,卻也同時夾雜著苦澀和美好。記得當時,我對一個叫納旦尼爾的男生有著強烈的好感,有些夜裡,我們會坐在他車上聊著玄妙又深奧的事情,現在想來或許會覺得可笑吧!我們曾經接吻,但當我看見他跟其他女生搭訕時,我總是會很戲劇性地哭著跑開或是憤而離去,但這就是年少之所以美好的原因吧!每件事都是如此悲傷、愚蠢、令人氣憤,但又充滿希望。我只想要自由,去體驗所有我能體驗的,成為一個有藝術天賦的人,一個機靈的人,或是某個很酷的人,但要怎麼做?我仍不斷試著理出頭緒。
Nomi, a sharp and intelligent girl,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conservative religious atmosphere that pushed her mother and sister away, leaving her and her dad on their own. Through her life as the Mennonite girl who often dreams of living New York with her entire family, she shows us the conflict between circumstance and love, rebellion and finding a particular faith, not in religion, but acquired through the disappointments she's faced. Nomi's voice, always with that teenage wit, slight-helplessness and uniquely teenage way of making this world always seem sweet and sad, leads us through this journey from start to end about a girl who has endured grief and confusion but all along she has kept all the memories and love alive with hope.
諾蜜,一個犀利又聰明的女孩,在一個極度保守的修道氛圍中出生長大。這道氛圍迫使她的母親和姊姊離開,只留下她,和她爸爸。身為門諾教派的孩子,諾蜜卻夢想著和家人住在紐約,她讓我們看見命運與愛之間的衝突、反抗,也讓我們發現一種獨特的信仰,它不是宗教、而是源自於她所面對的種種失望。諾蜜的話語總是充滿年輕人的機智風趣、小小的無奈,獨特的年少行徑讓這個世界總是顯得甜蜜又傷悲,帶領我們穿越關於這個女孩的故事──一個承受悲傷與困惑,卻始終保有所有回憶、愛、與希望的故事。
作者資料
泰維茲(Miriam Toews)
一九六四年生於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在奉行門諾教派的保守小鎮成長。高中畢業就盡速離鄉,先往蒙特利爾,再到歐洲遊歷。返鄉後,陸續取得電影及新聞學位。 著有小說《走運的夏天》、《有教養的男孩》及非小說《低蕩人生》,皆獲獎無數。目前為諸多廣電媒體(「加拿大電視台」「這種美國生活」「加拿大地理」「紐約時報雜誌」等)撰稿,得過加拿大全國雜誌幽默金牌獎。 《12號公路女孩》獲加拿大最高文學榮譽「加拿大總督文學小說獎」,並入選「加拿大吉勒文學獎」最後決選,當選2006年加拿大全國必讀書獎。
基本資料
作者:泰維茲(Miriam Toews)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
書系:小說無限
出版日期:2009-06-04
ISBN:9789866651564
城邦書號:YX0005
規格:膠裝 / 單色 / 320頁 / 14.8cm×21cm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