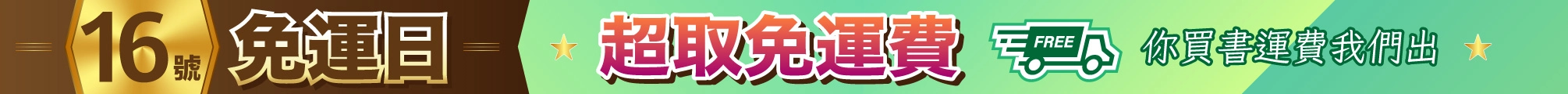- 庫存 = 7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什麼都沒有發生
- 作者:陳冠中(Chan Koon Chung)
- 出版社:麥田
- 出版日期:2016-09-01
- 定價:250元
- 優惠價:49折 123元
- 優惠截止日:2025年9月29日止
-
書虫VIP價:123元,贈紅利6點
活動贈點另計
可免費兌換好書 - 書虫VIP紅利價:116元
- (更多VIP好康)
-
購買電子書,由此去!
◎文/麥田責任編輯 林秀梅
|
張得志,香港頂級職業經理人,只愛賺錢,住五星級酒店,享受最好的美食、紅酒、女人……
香港回歸中國一週年那天,我午後起床,開始了應該沒有什麼發生的一天:沒有想做的事,沒有對自己或他人的承諾。心情,說不上好壞,沒有事情可以影響我的心情,在我悉心安排下,什麼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就算發生什麼,我也不在乎。 這是陳冠中極具批判性的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中的主角張得志。小說主軸描述張得志與女子沈英潔相識的風花雪月,與資本家托圖、雪茄黎等人的商業交際往來。張得志與沈潔英在超市無意邂逅、但卻不想對她負責;與生意人托圖二人在六四事件當日,一個選看「大話西遊」,一個避到國外享樂…… 小說塑造出經典香港人的形象:一個經歷香港經濟起飛黃金十年、不受羈絆、拒絕負責任的青年。 《什麼都沒有發生》書寫香港人的「問題」,也揭露當代的憂思--如果我們對身邊所發生的切身事情無動於衷,我們對自己生活的地方冷漠以待,那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核心價值留給下一代? 看香港人的問題,反思台灣,這是這本書值得推薦給台灣讀者的重要因由。 |
立即訂閱城邦讀饗報!GO
內容簡介
內文試閱
作者資料
陳冠中(Chan Koon Chung)
2013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 2009年小說《盛世》被譯成十三種外語,2013年小說《裸命》有四種語文,2015年小說《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獲得《紅樓夢獎》第六屆專家推薦獎,並獲選為中華民國國家文藝基金會《2000年至2015年華文長篇小說二十部》之一。上述三部小說皆曾入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華文小說。 其他著作包括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總統的故事》,小說集《香港三部曲》,文集《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事後:本土文化誌》、《移動的邊界》、《或許有用的思想》、《活出時代的矛盾:社會創新與好社會》、《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未完成的實驗》、《下一個十年》、《城市九章》、《是荒誕又如何》、《一種華文多種諗頭》、《波希米亞中國》﹙合著﹚等,以及改編的話劇劇本《傾城之戀》、《謫仙記》。 他於1976年在香港創辦《號外》雜誌,擔任出版人一職至1999年。1980年代從事電影編劇和監製工作。1995年他參與創辦台灣超級電視台,並為北京《讀書》月刊境外繁體版的出版人(1994年至1997年)。2008年至2011年他出任國際綠色和平總部的理事,現為香港大學名譽院士、台灣《思想》季刊編委。 陳冠中1952年出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四十歲後分別在台北住了六年、北京二十一年,現來回香港和北京兩地。 相關著作:《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陳冠中的時代文評集》《什麼都沒有發生》《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盛世》
基本資料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