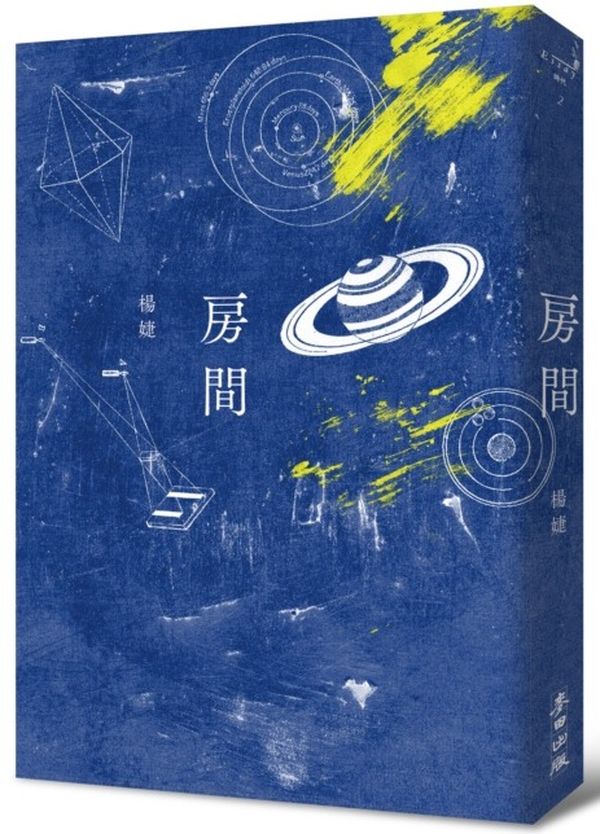內容簡介
◎陳芳明主編新時代散文書系——「Essay時代」推薦作家!
租屋啟事:這是一本居住、拆遷、尋人之書
她把自己蓋成了一棟違章建築——「我愛你,就像我愛房間。」
◎ 以「房間」系列散文迭獲大獎,《印刻文學生活誌》、《聯合文學》專文介紹,備受矚目新秀——楊婕第一本散文集。
◎ 透過一間間房回顧過往人情事景,文字雋永抒情,房間成了作者的對外觀景窗,涵納時間空間的流動移徙,藉由描繪房間輪廓物拾,不斷從中複寫記憶,觀照纖敏內心。
◎ 陳芳明主編,新時代散文書系——「Essay時代」出版主旨
當前台灣社會已經從權力的囚牢釋放出來,散文創作者的思考模式,價值觀念,內心感覺,已經與上個世代截然不同。他們筆下釀造出來的文字技藝,幾乎與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全然貼近。他們的作品,已經開始定義台灣文學的陌生圖像。其中的聲調、音色、味道、感覺,都足以容納時代變化的節奏。他們並列登場時,全盤翻新的散文風格也宣告誕生。
值此之際,麥田規畫推出的「Essay時代」系列,別具時代意義。此書系的選書,不限世代,不限領域,舉凡能體現當代社會的散文觀,以及反映多元議題的書寫,都是我們關注的對象。我們期許一個創新的文學發聲,在新的世紀展現應有的文化能量。——陳芳明
【內容簡介】
「楊婕或許正在建構一種個人的『直接存有學』,事關如何描述『自己的異鄉』。」——童偉格
「沒有不擠壓的房間,沒有不互斥的記憶,書寫即是追憶,追憶總是已經燒過揀選過的,像舍利子。托在掌上看,裡面是蜂巢般分割,蜜與灰同在。」——楊佳嫻
「不再執著於縫補。白色的生活,不過像又一次地震。妳將堅固地倖存。妳的愛與死。房間搖晃的恐懼。轟隆轟隆,妳會這樣老去。」
她說自己是被房間降生的孩子,十八歲離家,從此開啟找尋房間的旅程——套房宿舍青旅、共宿獨居借住,意外寫就一部情感建築學/私人住屋史:情同親人的房東、室友、偶然闖入的地下屋宇、看房奇遇、高原浪遊錯身旅伴、沿東海岸逝去的戀情……
房裡的物件,也成為途中最親密的伙伴——日日與塵蟎相擁而眠,整理箱收容淚水,黴如雪花覆蓋房間,見證潮溼的記憶。
最後明白,居住即遠行,我們都是自身的外來者——
「輯一:房間」記錄住過的各式房間與人情變故,開啟空間書寫、抒情散文新頁;「輯二:回收物」凝視房中大小器物,鏡子、護唇膏、棉被、毛巾……都被賦予活潑的生命,戀物/戀人/戀屋本為一體;「輯三:外掃區」剪輯房間周圍的鮮活景色,貫串半個北城的河堤、夜間捷運、巷弄鄰居、雨天叫賣饅頭的男子;「輯四:違建」書寫高原浪遊的迷離記憶;全書最末,「輯五:地契——霧中書」,則是留給遙遠的海邊房間、已逝去的戀人的絕密情書。
【名家推薦】
◎童偉格(作家)、楊佳嫻(作家、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暖屋序言
◎駱以軍(作家)、郝譽翔(作家、北教大語創系教授)、李明璁(作家、文化評論家)、林達陽(作家)、吳妮民(作家)喊燒出租
目錄
"「Essay時代」前言 陳芳明
推薦序 自己的異鄉 童偉格
推薦序 暗房與暖房──序楊婕散文集《房間》 楊佳嫻
輯一【房間】
房間
作親
曬衣情事
下三角
龜裂
鬼屋
女生宿舍
裸住
地底迷宮
零
流星群
看房
密室
輯二【回收物】
鑰匙
穿衣鏡
後書櫃時代
養樂多
蟲洞
禮物
熱敷墊
血清
免費擁抱
哈囉,門把
除溼機
椅子
拖鞋
毛巾
整理箱
初吻
黴
輯三【外掃區】
鄰居們I
鄰居們II
雨中婚禮
垃圾話
洞洞裝
潔癖
缺水
廢橋
氣象預報
溺斃
寂寞證
輯四【違建】
青年旅舍
安和橋
保養品
違建
孩子
瑣碎香格里拉
外遇
馬桶和客棧
自盡
剩女小番茄
輯五【地契──霧中書】
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第六書
第七書
第八書
一座太太
我們要前往遠方的麵包店
有時而盡
第二座太太:一千個夜晚
後記:而我是被冬日房間降生之人
內文試閱
房間
那是一座逃離的房間。
我在十二月中旬的午後入住,帶著幾箱雜物,和書。淺灰磁磚貼滿地面,圓燈、長燈由樑隔開,使天花板平添簡單的詩意,小夜燈藏在紋路蜿蜒的玻璃罩裡。靴夾與長靴是一對戀人,依偎衣櫃,深褐家具平衡了房間的寒冷色澤。另一邊,雙人床已接納柔軟的枕被,化為夢的搖籃。填滿物什的木櫃層層並列,彷彿會呼吸的小宇宙。
這些大小物件拼湊出來客,拼湊出我。我來到房間。
將物品整理好,天色業已暗下。窗外是大片荒地,我將屋室打亮,讓遠遠的燈火穿透明亮的玻璃窗,與房間合而為一。走進浴室拿魔術拖,從窗口拖起,很快沾滿灰塵毛屑,必須勤快清洗,才能消化地面的穢亂。
這座房間比我預估得髒太多了。
後來我幾乎每天重複這樣的步驟,並逐漸掌握訣竅:先用膠帶黏地板,再打溼魔術拖。布面擠滿灰塵後,去除較明顯的沾黏物。灰塵總是從角落湧生,故而我頻繁地打掃。清潔工作通常在晚上進行,日光燈一開,房間立刻綻滿簡潔的暖意。
有時覺得它過於乾淨,但唯有勤快整理,日常製造的凌亂方能復原,像一遍遍人生練習。
搬進房間前,習慣同身邊的人叨念各種瑣事,而這裡,泰半時刻是沒有聲音的。這座房間一如文字最私密的場域,飄滿我的習慣、氣味,不需任何言語補滿空白,我在其中。謹慎照顧房間,也感覺它悄悄保護著我——無論在房間裡,或身處他方。
我開始思考獨處的意義,重新建立定時定量的生活:三餐、寫字、打掃,日子變得輕鬆簡單。一向怕吵的耳朵,在這座靜謐完整、宛如星球的房間,益漸寬宏大量,外界的聲響,適度提醒了:生存。
儘管緩慢無聲的度日,仍切實存在著。
有時我在房間裡失神,過往如水流激越,崩解、碎裂。思緒湧動的狀態多在夜晚,冬日深夜滿是透明的冷,我獨自承受睡眠的輪迴,失眠時倒一杯酒,小口地喝。不容自我說服之際,便隨意翻閱木櫃的書,它們擁有各自的生命,曲折地陪伴房間。
我流連在一九九五年邱的蒙馬特,莒哈絲的童年西貢,費雷思殘忍的紐約,梵谷的星空。漫步遙遠土地,房間成了小小的萬花筒,足以旋轉天空。窺視關於傷痕祕徑,幽微的流浪譜系——悄悄遷徙著,在騷動的夜裡。
天色將亮,夢境如骨骼、如霧,煙塵般繚繞再散去。不管情節是好,是壞。
而這個季節最令人感覺安穩的時分,是陽光充沛的下午,我往往也能順利入眠。睡意滿漲的午後,拉上百葉窗,天空剩下條條亮線,像瞇起的眼睛,房間即成雨的森林。我在亞熱帶深冬的天光沉睡,棉被緊裹臉龐,如祕密的繭。遺失時間,遺失過往,僅是完整俱足的睡眠,在一個人的房間裡。
半昏半昧,有些知覺仍會滲入被窩,散溢、流竄。但我被房間包裹著,一切遊走在意識邊緣,失焦地帶。會記得的是溫度的變異,不論身體或情感,雖然房間內,記憶已經散失名字。
總在起身後,靜靜回想,抑或什麼都不想,僅只醒來。懷疑自己是否真正清醒過,說不定搬進這座房間以來,我始終困在凍結的夢境而不自知。
直到那天下午,我似乎醒過來了。
房間依然是亞熱帶的冬天,照耀寧靜的林中風景。枕被如懷抱,我密實地蜷拱被窩。醒轉,聽見窗外敲敲打打的聲音,夾雜對話,躺在床上聽了一會,然後穿上外套,趿棉拖鞋,拉開百葉窗。烘得明黃的陽光斜斜倒入,臉上升起好溫和的暖意,探頭望下看,三五工人帶器械挖土,不時用閩南語閒扯,相互玩笑。
我疏於語言,卻在窗前端詳許久,看如此家常、滿是生命氣息的畫面,在陽光暖燙的下午開展。北臺灣的冬季潮溼寒冷,工程固定在放晴的日子進行,施工聲響每每伴隨晴天,窩在房間做事,聽窗口洩進施作聲,與工人笑語,漸漸得到踏實的力量。
每天工程項目均不同,包頭巾的婦女來弄草蒔花,開窗能聞到新鮮泥土的氣息。倒水泥那幾日,車上還掛著小旅館的廣告,宣告人性的樸直。最嘈雜是怪手運作,或處理建材鋼筋時。
也有一次候選人的宣傳車熱熱鬧鬧開過來,重複廣播再陽春不過的內容,至動工處掉轉駛離,再熱熱鬧鬧離去。我覺得那段景象像卓別林的默片,或聖修伯里筆下不同星球的主宰者,荒謬中捎帶一種親切的笑意。
窗口景致不斷變化,胡亂臆測而不得頭緒。幾回遇到房東,想詢問工程,閒聊一陣總忘記提。我決定繼續默默注視,猶如一個不成文的、和世界的約定。施工地帶由雜亂到整齊,再由整齊到雜亂,來回往復,形成某種韻律,多像這座房間。
當我習慣觀察工程進度,如同規律的作息,力量也一點一滴越過往事,回到手中。我常對著變換的工地沉思,從曖昧的光暈領略意義——關於崩毀、傷害,更內在自我的種種,皆如風如煙灌滿房間。
施工總在天色完全暗下前停止。入夜,燈火投影在玻璃窗上,外面的世界與房間交疊,既親密又空曠。日光燈在一天中開啟的時段越來越長,期末將至,我夜夜讀書準備考試,更多工夫凝視房間細節,不若初來生疏,卻感覺一切過於爽淨。
於是學期結束,我重新布置房間。
我跑遍家具行,挑選一張紅色絨布沙發,安放桌旁,可以思考,可以休息,或無所事事,單純被簇擁。沙發底部四輪撐起,便於清掃搬移,沉穩的豔紅預告了季節遞嬗,與心情移轉。
夜裡窩坐沙發翻閱木櫃的書,它們又再度來到我身邊。幾天後,一幅複製〈星夜〉在牆上綻開,流轉一八八九年法國小鎮的夜空。那是梵谷寂寞艱難、幾近殉道的自我實踐。絲杉孤傲地伸入天空,雲朵徘徊在山巒邊緣,人間煙火垂首。星空極盡華麗,天體的運行生動莊嚴,或者,恍如漩渦,埋伏不被理解,也難以訴說的心事。
梵谷被療養院的房間困住,而在房間裡,他看見純淨燦爛的星夜。獨居者無意逃離人世,然而人世未能擁抱他,因此梵谷以油彩將自我堆疊,寄託給這幅被千千萬萬遍複製,如今懸掛房間的星夜。
縱然看向窗外,我所見僅是疏落的星空。而暗沉的星光無法照亮工程的變化。
將房間打掃乾淨後,我收拾行李,拉上百葉窗,讓房間伴隨所有物事一同沉睡。雨林的顏色漫上房間,告別祕密而安定。
分離的日子不太記掛房間,因為我早已相信它的承諾,偶爾在他方想起,只覺得情感也有屋舍的個性。那些從生命底層無聲湧出的愛,曾經一脈相牽,曾經直面擁抱,然後成為窗,成為門,成為記憶的房間。
但就像人的遷移,我從宿舍搬進招展在荒煙蔓草邊的房間,隱隱期待春天的來臨。
再度沿原路回返,已是二月底微涼的下午。漫長冬季消融,西天太陽將街道染得金黃。我一路想像孤獨的房間景象,及窗外工程的變化,也許入夜將星光燦爛,或僅存淺睡之紅。將拐過街角遇見房東,寒暄幾句,房東略帶歉意地笑笑,道施工完畢,東西都做好了,之前常常吵到你們不好意思。
我聳聳肩,微笑然後轉身。
沿路花朵綻放,稀疏卻堅定地向遠方荒地蔓延。這些初生花草不止開在路上。風拂面吹來,天空隨之搖動。我繼續向房間走去,步伐更加穩定,或許可以預期,會有一場大規模的詩句,在新的景色爛漫盛開。
作親
八月三十,二○一二。搬家當日早晨,叔叔來清點家具結算水電費,進屋探看四周,誇我維持得好:「女兒的房間果然乾淨!」叔叔在桌前記帳,零散道些以後回來請我吃自助餐的話,發出一貫的嘿嘿笑聲。我不敢看叔叔,背過身弄東弄西。搬家公司的先生將物件一箱箱往外搬,房間掏空,叔叔事畢,喊我名字說聲:「楊賊再見啦!」
我揮揮手,忍不住哭出來,叔叔溜身俐落地走了。
那批最初帶進房間的行李,以及幾年來添加的種種,都層疊打包塞到車裡。我和那些東西一併坐上車,下斜坡,分分秒秒遠離了房間,遠離店面。車輛加速,風景一窗窗快轉,還是不能無縫遷徙。
前座搬家公司的先生笑了,他從沒遇過客人搬家哭的:「感情太豐富!這有什麼好哭?人生不就是搬來搬去,妳以後就習慣了!」
前幾天買的花生塞在包包裡。我一邊注意花生不要壓碎,一邊手撐拉環,顛顛簸簸下山。轉往臺鐵,五十分鐘出站,走過站前圓環,等熟悉的號碼駛來,開上位在郊區臺地的校園。
踏進消夜街,街底斜坡向右,繞過已不屬於我的房間。巷弄盡頭,兩點鐘方向便是自助餐了。
離晚餐尚有一段工夫,鐵捲門半拉下,我遠遠走近,來路程程退開。撥打叔叔手機,接通道馬上下樓,幾分鐘後鐵捲門升高,叔叔阿姨彎身出來,叔叔略發福些,阿姨頭髮燙捲了。他們未料我要來,我拿出花生,有些緊張,阿姨先發話:「哎唷妳怎麼知道叔叔最喜歡吃花生!妳跟叔叔慢慢聊,阿姨去煮飯!」
我實則誤打誤撞,像簽約那天第一次踏進自助餐。
那是三年前的下午。初冬微寒,老舊店面顯得溫暖,我和母親看過房間,隨阿姨來到店裡。店內光線昏暗,玻璃印滿刮痕,霧氣般掩住街景,非用餐時段,不見客人。
阿姨端出一盤薯條,母親正要推辭,阿姨說不是特地炸的,早上小兒子顧店,當作給他的獎勵,剛好多炸一點,還想夾什麼菜自己拿,吃飽再走啊。我們禮貌性拿了幾根薯條,離去時還剩少許。食物的氣味混合出周邊氛圍,自助餐未有多餘陳設,毫無宣揚。
「我們會把她當自己女兒照顧,你們放心啦!」阿姨告訴母親。
阿姨嬌小,終日低馬尾搭圍裙,在最底的半開放廚房忙碌。叔叔身量亦不高,POLO衫色彩樸素,帶點啤酒肚,夾克配香菸,戴半罩安全帽送便當。叔叔阿姨長年賣自助餐,出租兩棟學生套房,一新一舊,舊房子不知年分,新房子在我搬入前兩個月完工。
從房間到自助餐步行僅需三分鐘。剛搬進房間,我每每造訪自助餐,皆為房間細瑣,進去店面總見煙氣蒸散,叔叔阿姨揮鍋鏟端菜盤裡外出入。炒菜喧囂,到廚房門口他們才發現我來了,通常阿姨掌廚,問候一聲繼續蒸煮,叔叔負責招呼,管房子的事歸他。
那段時光我中午一向早吃飯。有幾天上午的課十點結束,一段空檔正好處理雜務、買午餐。我常趁那時去店裡,每回叔叔皆問我買便當,我的脾胃挑食而專情,相同菜式能吃上個把月,已有固定店家。起初婉拒幾次,但早開的店不多,餓就加減買,時日久了挑到合口味的菜,便養成吃自助餐的習慣。叔叔得空就和我聊幾句,在那些裝飯揀菜的步驟裡日益熟起來。
來得太早,慣吃的菜還沒擺出來,叔叔阿姨一邊炒菜一邊包工廠訂的便當,抽手替我盛飯端菜。去的次數多了就更家常,讓我進廚房,蹲在推車旁翻揀,錢擱櫃檯,自行打包。便當都算我便宜些,倘若叔叔拜託我貼房子的布告,那次就不收錢了。
我的便當固定焢肉配高麗菜,不時也換梅干。阿姨是客家人,梅干扣肉煮得極香,我不曉得道不道地,一吃就愛上。梅干扣肉大約兩週賣一次,不定哪天會有,得知我愛吃,每逢去店裡,假如隔天要賣,叔叔便會提醒我一聲,有一次沒過去,叔叔特地打電話來。
偶爾過節,他們便替我加菜,夏天的粽子,秋天的柚子。夾完便當後,阿姨會小聲叫我留步,等別的客人走了,再塞給我帶回房間,節慶就爽口一些。
我幾乎天天行經自助餐轉回房間,過了店招,便到達房間所在的巷弄。我時常停下腳步,為房間細務踏進店裡,沒上門,也碰到叔叔出來送便當,熙來攘往的街道,他會用臺灣國語越過重重人群不太標準地喊我:「楊賊!楊賊!」每當我低著頭非常疲倦地走在路上,思緒晃到哪裡浮浮蕩蕩,一輛機車過去,我便被叔叔的招呼喚醒,不動聲色落了地。
我在那座房間學會照顧自己。基本的食衣住行,面對自我,孤獨。無論何種技能,皆比同齡之人晚熟,凸槌時,少不得叔叔阿姨前來救火。
一回洗衣機故障,脫水功能失效,打開蓋子,每件衣服都浸著水,重洗再丟烘衣機,連烘兩次仍溼淋淋,只好整籃衣服滴水搬回房間。阿姨來,說之前有房客用釣魚法洗衣,現在衣量超載就會壞。阿姨踏進房間,見曬衣桿滿滿兩排,教我一次該放多少衣服,踩過走廊、電梯灘灘水窪,一句責備也無,只問花了幾塊錢洗衣,塞鈔票到我手裡。
保險絲燒壞,房間跳電,叔叔提來照明燈,告訴我店面二樓有空房,晚上不方便就去睡。我鑰匙用了一年都亂轉,有一天缺乏手感便堵在門外,以為門鎖生鏽,倒油也開不了,正是晚餐時分,叔叔放下事務,風風火火過來,一扭就開。叔叔嘿嘿笑幾聲,教我用鑰匙,回店裡繼續忙碌,叔叔道:「妳念文學的,生活的事比較不懂啦!」
自助餐休息時段,叔叔常來巡視、打掃。見房間燈亮著,便會敲門,拿掛號信、交代房間的事,有時不過打招呼,也沒說什麼。叔叔走前,總笑著告訴我:「那叔叔先回去忙了嘿嘿!有事情再打給叔叔!」
鏡頭倒轉。大二那年初夏,夜半我在房間痛哭,敲門聲驀地響起,只得硬著頭皮開門。叔叔站在門口,看了我一眼,輕聲叮嚀:「爸爸媽媽不在這裡,妳就把叔叔阿姨當成自己的爸爸媽媽,有什麼困難都可以講,我們能幫的就幫,不要自己悶著,這樣不好。」
過幾天去買自助餐,閒聊幾句,叔叔問心情好多了嗎?「叔叔知道妳是個用情比較深,比較細膩的女孩子。」我暗暗吃驚。我向來只跟叔叔阿姨說些生活瑣事,天氣、食物、居住、考試,關於情感,關於內心,隻字不提。
那些日常片刻,叔叔用他的方式理解了我,即便他所知不多,我所談亦不多。而那樣的理解,在長年獨居、不喜同群體往來的大學歲月裡,已是我與周遭人事最密切的關係了。
我對人際紛擾戒懼,曾有過的幻想與渴望,早隨之灰飛湮滅。但和叔叔阿姨相處,一切僅是簡單的細節,往來之間,終能踏實地觸及自我。叔叔阿姨是很尋常的夫妻,哪條巷弄皆會出現的一對夫妻,因為尋常讓人親近。
那幾年難以言說的青春起伏裡,他們的素樸,成了提點我的一種要領。
也就是那段日子,我為房間寫了一篇散文,細述裡外物事,得了文學獎。叔叔在結尾軋上一角,我想叔叔阿姨不看這些,便不太提起。
搬家前幾天,我把兩年前的作品附在卡片,拿到店裡交給叔叔阿姨。阿姨曾笑地靦腆告訴我,她年輕時也喜歡讀詩,席慕蓉噢。這些年的蒸煮炒炸中,那款脆薄的興趣應該也淪為一種過時的菜餚。說不定那篇散文將被棄之屋角,但這是我跟他們告別的儀式,不得不了。
回想那座房間,雖則裝潢好、屋況新,但位處馬路旁邊,我神經質地怕吵,每隔幾分鐘車開過去都不得安寧,近處又陸續蓋起幾棟新房子出租,敲打聲終年累月。可我一直住著,不容再住才搬出。
我走得晚,同一批房客六月畢業季就遷離了。那陣子去買自助餐,叔叔常念叨著說:「妳也快搬走啦,好像女兒要走一樣。」
離開後,我才察覺,那擺滿飯菜的店面,比起房間,更先給了我居住的感覺。房間跟自助餐始終那般接近,處置房間事項,往往在自助餐交辦,領房間物什,也和熱騰騰的便當一道拎回。在自助餐以外的地方遇到,他們常說,從店面忙完過來,等會要回店裡。找話題問候叔叔阿姨,亦圍繞自助餐——幾點打烊?哪些客人上門?煮什麼菜?
我幾乎錯覺自己也在店裡有過一間房間。
剛上研究所過得並不開心,和叔叔阿姨未有聯繫,僅有一回接到電話,看來電顯示是叔叔,以為問我近況,結果只是通知我去拿寄到舊地址的體檢表,講幾句就掛了。
後來零碎聽見還在那裡的友人傳來音訊,似乎每逢中文系的人上門,叔叔就容易提起我。叔叔告訴同學:「她就像瓊瑤小說的女主角似的!」阿姨有了臉書,想加我卻找不到,送出交友邀請,阿姨遲遲未回覆,或許仍對電腦太生疏。
叔叔阿姨知悉我申請上交換學生,忘了日程,向同學問起我過得好不好?彼時我尚未前去交換,方短期旅遊回來,剛從異地寄出明信片,無須多加解釋,他們收到便會明曉。
記憶窩裡反,距離山重山。人生總是如此,但我對記憶和距離執著。
學期過完,回到那條街。房間是進不去了,自助餐的鐵捲門緩緩拉開,就跟簽約那年冬天一樣暖。陳舊空氣裡,叔叔說起,上次暈倒送進醫院啊,現在要多休息,週六不開店了。叫我包個便當吃,傍晚還得趕回學校,叔叔便改口到隔壁買飲料請我喝。
這幾天才跟阿姨念到我:「在想打個電話給妳,又不知道怎麼打就沒打嘿嘿!」聊起搬家那天——「叔叔你轉身就走了欸!」叔叔道他不敢看我的表情,才趕快走掉,回到店裡就告訴阿姨我哭了。「妳是第一批房客,住最久,比較有感情,我們和妳緣分深啦!」
叔叔交代,經過附近要回來看看,提早講一聲煮梅干扣肉等妳來,再回去就住那棟房子,會替妳留房間。「不管什麼事,工作啦嫁人啦都要告訴叔叔,妳結婚叔叔一定包紅包。」
兩天後,夜裡手機震動,阿姨傳來簡訊,百來個字,說那天見到我很高興,祝我早日取得碩士學位,一切順利。
幾年屋事,叔叔阿姨一向電話、當面告知,我第一次收到來自他們的簡訊。在這輕薄的年代,仍然有人,打簡訊像寫一張卡片,有著隆重的心意。叔叔阿姨不雪月風花,也不詩詞書畫,他們如是不擅表達感情,因此每一句都真實。
叔叔阿姨替我守住了對那裡的眷戀,而我曾經以為自己將只是無情之人。
我何其後知後覺。無數次和叔叔阿姨聊及房間細節的時刻,錯覺將真正關乎自我的種種,遮蔽或延後了。當時未曾提及的願望和困擾,在時間磨洗下,終於揭開面貌,還給生活本身,變得不再重要。
如今我在他鄉租住,經常不合時宜想起往事。重讀在那座房間寫過的字句已覺陌生,那些十九二十歲的心事,從離居到安居的過程。
房間歲月終煙散在平凡的日子裡。學生年年輪換,有朝一日房間勢必不認得我這第一個住客,但下次回去,我總能在那黯淡裡溢著香氣的店面去來,不像外人地,好好夾菜,吃完一頓飯。自助餐的陳設,將一直熟悉溫暖,一如已經沒有契約期限的房間。
彼時屋室都將亮起,讓身分藏隱,也讓身分清晰。
後記
幾年後我隻身旅行,途中到成都。叔叔阿姨的兒子兒媳在成都工作,大我幾歲,從未照面。阿姨再三叮嚀,說小女兒要過去,叫哥哥姊姊照顧我。
我和哥哥姊姊約在傍晚的鬧街。那時我已離家數月,許久不見親人,一看到哥哥姊姊便覺安心,姊姊和善穩重,哥哥長相像極叔叔。
他們帶我去吃火鍋。聊著聊著我就哭了,說起從前叔叔阿姨對我的照顧,我現在這個樣子,怎麼回去看他們?哭著哭著又笑了:「十九歲對著叔叔哭,沒想到二十四歲,來這裡還在你們面前哭,真沒用。」
哥哥說,難過是一定的,妳哭,代表妳把我們當自己人。哭沒有關係,不用限制自己只能哭一次、兩次,想哭就哭。「我感覺得出他們很疼妳,剛剛妳提起我爸媽,我其實也很想哭。」
零
他穿五顏六色的衣服來接我,內襯棉T搭厚夾克,組合拼湊。我弄不清他究竟穿什麼,坐上後座,左邊卡著一團衣物,色系太雜,我分不出那是包包或衣服,只覺得前面的人披著一塊百衲被。
傳統的百衲被是方形菱形的,剩餘布料裁切拼縫,節省溫馨。而我還不能描繪布被底下他的形狀,應該是圓形的,O。內裡銳尖有所損破,歷經針工,但對我會是圓形的,沒有凹口。O。
圓形的O。
O第一次載我回家,我行禮如儀打開外門,輕輕關上(怕他嫌我粗魯),O在原地,靜悄無聲。我上二樓,踏過一階階臺階,以為會聽到O發動車子的聲音卻沒有。步入走廊,拿鑰匙開門,進房,掐電燈,才聽見O的機車聲。我沒到窗邊看,可我曉得O跨坐上車,轉動車把。他終於走了。
說起這件事,O以為我靠在窗戶偷窺,我連進門前回頭看一眼都不好意思。這是一個聽音辨位的故事。
也有無數回家的遭遇。其他朋友載我回來,都是到巷口就停,我會說我住在這條巷子裡,自己進去。縱然巷弄被兩條極黑極黑、踩過的人總要皺眉嘆危險的小路包夾,但巷弄本身是單純的,不長、又有路燈,夜裡並不可怕,他們聽了便在巷口把我放下。O載我回來時,我也照例告訴他,且猶豫是否要讓O知曉我住哪。
O卻很有耐心地問我住哪一間房。騎進巷弄,車速放緩,一幢一幢,我說到這裡就可以了,O仍繼續騎行。我不得不告訴O我住哪,用手指一指樓下信箱(避免指認面對巷弄的房間),假作隨興地陳述,恰如我只是在介紹一間好吃的雪花牛或泡芙,而我非常喜歡吃雪花牛和泡芙。
欸,我喜歡吃的東西在這裡。
我長年住居,賴著賴著像要病了的房間就在這裡。
我不確知O懂不懂得,指證自己的房間於我是多麼私密的事。我清楚記得誰知悉我的住處,誰進過我的屋子,誰有,誰沒有。我能在別人寄明信片時輕易給出地址,那僅是一串缺乏溫度的街巷名稱和數字,但我舉起手臂,指向房子,打開破舊的大門,走上階梯,彼刻,隱蔽在巷弄的房間,會和我一樣戰兢。
後來問O,為什麼待在原地那麼久,O說確認妳到家了。從巷弄到房間,一道樓梯、三扇門,如若短暫的距離,O認為我會失蹤?還是他看出我的居住之地並不單純,房間內外暗布的重重甬道,O預知多少?他有把握穩健步行而不跌倒嗎?
O,隨處可被指涉,重整或尚未出發的符號,連物質都不是。
O其實是一首偶像劇主題曲。男主角將自己燃燒殆盡去愛女主角,殘破已盡之人,竭力保護和他一樣衰頹的生命,這是多麼感人的事情。
前陣子我又看完一部電影。電影裡,O是一種舊式戰鬥機,男人自願駕著那架飛機死去。畫面末了,男人的眼睛張得好大、好大,靠向鏡頭越放越清晰,聚焦瞳孔,卻能感到四周狂暴的風和被移動的天空。在O之上,他的雙眼興奮地就要逼出淚水。
而他永遠不會再流淚了。人們喜歡說:歸零,對O這個數字,我的朋友多有所執迷,甚至青春期曾懷抱活到三十就不要再老下去的念頭。可是,沒人到了三十歲真的去死,我的朋友,一個都沒有。
我從不是那樣的人。我並不抱持三十歲一切就能歸零,或不能再被零收整的想法,這不表示我務實,我是根本不想擁有數字的概念,不想開展。從O為1,為9,為人。生而為O,我很抱歉。
我曾相信一切都能成為O,而今再也不會了。
這樣的我在秋天開始跟O說話,我們說話的月分也有一個O。O是好欺負的人,底限之前,一切都無所謂,一旦逼近O,則不會絲毫讓卻,他要守住他的O。凌晨講電話時,O如是說。房間裡,我握著手機,想告訴O而沒開口。
(O,這座房間,可以承受死亡,卻不能改變死前的線條了。)
有O的十月,房間的洞口寧靜地深邃,必須一步步探路。我知道O下次來,就會踏進房間。他將看見房間座落走廊盡頭,夜裡開窗,目睹對面樓房一道又一道鐵柵,天亮,落進來的光也就一條一條,我住在被分割的長方畫面裡邊,日夜顛倒。
而他是房中唯一的O。圓圓地,就像眼睛。一張一閉,但永不變形。
這是我最後一個,O的祈禱。作者資料
楊婕
1990年生,牡羊座。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台中文學獎等,登上《印刻文學生活誌》「超新星」、《聯合文學》「新人上場」單元。另入選《創世紀六十年詩選》。作品散見《印刻文學生活誌》、《聯合文學》、《中國時報》、《聯合報》、《人間福報》、《幼獅文藝》等。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