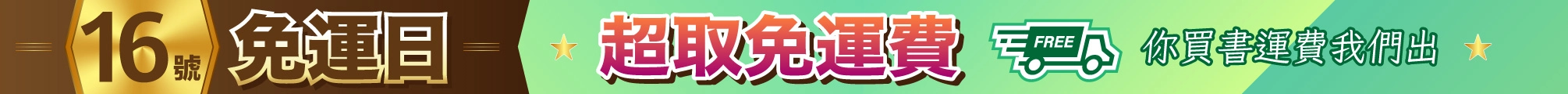- 庫存 = 3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本書適用活動
分類排行
內容簡介
她的信念只有:
「我不會停止發問,我要繼續做理所當然的事情。」
◆知名記者、公民媒體 掛名推薦
翁琬柔|國際新聞記者
張珮歆|文字工作者
◎ 日本新銳導演 藤井道人 執導,電影/NETFLIX日劇《新聞記者》原著、角色原型
◎ 改編作品被日本媒體盛讚「勇敢之作!」
◎ 訪問日本第一位 #Metoo 公開受害者.伊藤詩織
◎ 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菅義偉拒絕回答問題的女記者
◎ 《紐約時報》稱其為「之於新聞自由,是有如國民英雄一般的存在。」
即使被日本政府抨擊、封殺也在所不惜。
只為守在真相門口,不斷提問——
◆書籍內容介紹
日本知名記者.望月衣塑子,無疑是日本媒體界最特立獨行的存在之一。
她總是一身簡易套裝,在各大採訪現場高舉發言的手,面對政府高官和事件黑幕也毫不動搖。她為了拼湊真相的拼圖而不斷發問,但對於崇尚合群、集體主義的日本社會來說,此舉無疑是在挑戰權威和眾人觀感。
有人說,她譁眾取寵;也有人說,她勇敢堅定。
卻只有她自己知道,當年為何選擇成為追尋真相的新聞記者——
◆帶你認識最勇敢的記者.望月衣塑子
【不停發問的女記者(上)】窮追不捨的她 讓日本官房記者會修改採訪規定】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720inttokyoshinbumjournalistone/
【不停發問的女記者(下)】其他記者像「書記官」 她打破窠臼被批愛作秀】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720inttokyoshinbumjournalisttwo/
目錄
序言 2
第一章 對記者的憧憬 9
熱衷於演戲的時期 9
與母親到小劇場 9
遇到一本書決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10
來自記者父親的一句話 12
追尋吉田瑠衣子的腳步 13
對TOEFL成績感到愕然 14
在留學地受重傷 15
在大學的專題研究感受到核威懾理論的「陽剛感」 16
求職的筆試成績全軍覆沒…… 17
在新人培訓階段配送報紙 19
馬上後悔當記者 19
穿高跟鞋和裙子的新聞記者 21
與縣警幹部的早晨馬拉松 22
「現在立刻下車!」 25
第二章 宣洩噴發的熱情 26
殺氣騰騰挑戰警方的前輩記者 26
是否帶著熱情認真在思考 28
警方因收賄事件來探口風 28
跳脫縣版! 29
讀賣新聞的邀請 30
從極機密管道入手的非法獻金名單 32
領先友報與被領先 33
因為懊悔而打電話罵檢察廳幹部 34
被搶先就搶回來 35
被特搜部傳喚 為期兩天的調查 36
「東京新聞寫太多東西了」 38
轉調內勤 39
整理部教導我的另一種新聞 40
父親對跳槽第一次表達意見 41
將焦點放在武器出口 43
連吃閉門羹 44
第三章 當旁觀者就好嗎? 45
直接向編輯局長建議 45
菅野完持有的收據 46
母親有異狀 47
「謝謝你,謝謝」 48
成為新聞記者的理由 50
朝日新聞獨家:「政府的意圖」 51
真子公主報導的背後 52
我所尊敬的讀賣新聞居然…… 53
對「貧困調查」無法理解 54
區分事實與推測的一絲不苟 54
與和泉輔佐官之間不算淺的緣分 55
教育基本法的修法與安倍晉三紀念小學 56
只能親自出馬 58
「我是東京新聞的望月。」 59
第四章 自己能做什麼? 60
壓抑不住的念頭 60
男性特有的理解? 62
與公司內的幫手一起 62
與看不見的權力對峙 64
興奮迎接記者會 66
「麻煩簡短發問」 67
「因為我不覺得有確實得到答案」 68
記者同行的怨言 69
超乎想像的擴散 71
受到聲援而感受到鬱鬱寡歡 71
第五章 超越獨家主義 73
突如其來的劇痛 73
官邸的各種對應 74
記者俱樂部制度的極限? 75
可疑的警告與身分查核 77
來自產經新聞的取材 78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79
國井檢察官涉及冤案 81
日齒連事件以來的因緣 82
揭露對方想隱瞞的事情後 83
跳脫獨家主義 83
兩位可靠的記者 85
為了擴展人脈 87
後記 89
序跋
序言
有如拼圖一般
我常會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簡訊,從二〇一七年六月就開始頻繁使用。
但我不是用來傳簡訊給其他人。我早上七點起床會大略看一下早報的標題。然後準備早餐給孩子們吃,同時播放著電視新聞或資訊節目。
為了不忘記早上不經意看見或聽見的那些引人注意的標題或字幕,我會寄簡訊給自己保存下來。
這是事前準備的一環,為的是參加上午十一點舉行的菅義偉內閣官房長官的例行記者會。
我在六月六日首次出席了官邸的發言人例行記者會,這也是為了親自去確認狀況,看是否跟在電視上或首相官邸網站上一樣。
幾乎各家媒體的政治部都會出席官房長官的記者會。政治部主要負責採訪內閣或國會議員,並傳遞國家的政策或外交訊息。一方面,我隸屬的社會部則是採訪事件或未經證實的嫌疑,也很常會和政治家或檢察官等權力對峙。我身為社會部的記者,在此之前從未出席過官房長官的記者會。
那天我只是想先去看看氣氛,並沒有打算發問,但因為記者會三兩下就要結束了,我不由得舉起了手來。
「我是東京新聞的望月。」
我依照在發問前必須報上媒體名稱和姓名的規定,問了幾個關於文部科學省前事務次官前川喜平的問題。途中,記者會的男司儀提醒了我。
「麻煩發問簡潔一點。」
事後我自己也確認了一下,我的發問不僅很長,而且連我自己都覺得很煩人。同業的外子也打電話訓斥說「發問要簡潔有力」。
之後我也在各種場合被人提醒,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也產生了變化,開始保存那些比較吸睛的用詞淺字,因為或許能在詢問菅官房長官時當作參考。
我還沒自我介紹,我正在東京新聞社會部擔任記者。東京新聞是中日新聞集團在東京地區的地方報紙,整個集團以東海地區為中心在一都十七縣發行報紙。我有一個獨特的名字叫衣塑子,這是源自大正時代的詩人荻原朔太郎,因為我的母親希望我成為「能製作或創造一些事物」的人。
進入新聞社後,我在各辦事處沒日沒夜採訪了許多事件。育嬰假結束後我隸屬經濟部,於二〇一四年日本武器出口解禁後採訪了當時的現狀。
之後我又回到社會部,從二〇一七年七月開始,成為森友與加計問題的採訪團隊成員,追查其真相並在官邸記者會上持續發問。
首次出席非我主戰場的官房長官記者會後,過兩天我再次出席記者會,提問次數也比前一次更多。我拿出成為新聞記者後就不停被灌輸的記者精神,總共問了二十三個問題,平常快的話不用五分鐘的例行記者會變成了三十七分鐘。
新聞記者的工作如同製作拼圖,必須讓對方承認真相,並進一步查證——我是被這樣教導的。
在採訪一個事件時,你不會一開始就聽到真相,你要以發問會被否定為前提,不斷丟出疑問。
從我還是新人的時候開始,我身為記者的基準點從未改變。在當初覺得非我主戰場的官邸,我照樣貫徹了自己的風格。
從兩個記者會觀察到的事情
我也出席了首相安倍晉三的記者會。常會結束後,六月十九日傍晚首相官邸舉行了記者會。
「望月妳舉手發問看看啊。」
自由記者岩上安身對我說完,又補了一句話:
「可是他們絕對不會點妳。因為我出席了五年左右,每次都舉手發問可是從來沒被點到。」
據說安倍首相對媒體的好惡極端鮮明。我還聽岩上說在記者會上會被司儀點到的只有NHK、日本電視台、TBS、富士電視台、讀賣新聞或產經新聞等少數幾家媒體。
聽說還有NHK的記者沒有舉手卻被點名發問。而且要問什麼大多事前會提交,政府人員會配合訪綱製作回答,再由安倍首相當作自己的話照著唸。
我想這只能算是一切照著劇本走吧。這種記者會有什麼意義呢。我實際嘗試舉手,真的沒被點到。
反之,菅官房長官的例行記者會就不一樣了。
「不是你所說的那樣。」
「完全沒有問題。」
這樣的回答曾幾何時在坊間被稱為「菅話法」,反覆用冷淡的態度平靜說出定型句,片面中斷溝通的手法常會讓人感到煩躁。
即便如此,只要記者想舉手發問,在記者會上就會確實被點到。不會特定媒體,也不會要求你事前提交發問內容。
但不知何時開始,宣傳官會用「最後再一題」或「最後再一個人」的方式明確終止發問。因為沒有得到答案,所以我無視宣傳官繼續舉手後,
「以上記者會結束。」
居然是內閣記者會幹事社的某位記者擅自結束了記者會。明明同樣都是記者……?這點我在本書會提到,總之我感受到記者俱樂部這個制度的極限,當天甚至感到意志消沉。
(譯註:幹事社是負責與首相官邸聯絡的窗口新聞社,作用是統整各家新聞社的問題與意見。)
持續做理所當然的事情
話雖如此,也不能不去官邸或停止發問。
「妳要持續到何時?」
朋友和認識的人常會對我這麼說。
七月我因為腹部劇痛,染病躺了幾天。壓力是其中一個病因,我可能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一直感受到外在壓力。
這樣的狀況讓幾個朋友看不下去,開始擔心我。但既然能和政府或官邸連結的只有菅官房長官的例行記者會,那我只能要求自己每天上午場或下午場出席一次。
目前的階段,我不認為政權或官邸已經消除了森友加計等問題的疑慮。如果沒人問,那只能由我發問。
我並非自以為是社會派,也沒有對自己所處的狀況感到得意洋洋。只要覺得奇怪,不管發生什麼是我都會緊咬不放,直到弄懂為止。我身為新聞記者,中心思想就是揭露警察或當權者想隱瞞的事情。為此我會帶著熱情,不停反覆發問。我想做如此理所當然的事情。
現在媒體會報導我發問的模樣,我也得到許多雜誌或電視的採訪,以及演講的邀約。東京新聞也收到一般民眾許多的加油打氣。我在收到鼓勵之外,也收到了許多抨擊、可疑電話或間接壓力。
不過,雖然有人把我說得像是正義的英雄,或是把我貼上反權力記者的標籤,但我感覺自己與這些頭銜是有距離的。
我身為記者,只是在做從新人時代就被教育的事情,而身為個人,我是一個容易帶入感情、聲音又大的冒失鬼。
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包含我自己的生平在內,上天給了我許多寫作的機會。新聞記者的工作為何,我從前輩和取材對象那裡學到了什麼——希望大家在理解記者本質的同時,也能覺得「望月這個人真有趣」並對我抱持親近感,這會讓我感到很開心。內文試閱
第一章 對記者的憧憬
熱衷於演戲的時期
每當回去看小學的畢業文集,我都會面紅耳赤。當同學用文筆傾訴對畢業的想法時,我卻毫不害臊地寫了這麼一句話。
「我要當演員!」
這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但其實我當時相當認真。
我在靠近埼玉縣的東京都練馬區南大泉出生長大,母親在小學三年級帶我去參加兒童戲劇教室。四年級我進入練馬區主導的練馬兒童劇團,不知不覺開始熱衷於演戲。
我很期待每週一次的練習。發音、讀劇本或放感情練習演技,每次約兩到三小時。最大的目標是每年一次的發表會。發表會的舉辦地點是練馬文化中心的小音樂廳,可容納六百人左右。事前會夾雜唱歌或跳舞,反覆進行好幾次採排,算是相當正式。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年級的時候,演出的音樂劇是《安妮》,我負責演主角。花了三四個月準備,暑假還進行了四天三夜的集宿,隨著正式演出越來越近,我對練習就越發熱衷。
女主角安妮相信父母還活著,逃離了孤兒院去尋找父母,過程中被警察發現帶回孤兒院,後來受到百萬富翁奧利佛.沃巴克斯的喜愛,還在他的家中度過假期。故事中還能看見安妮告訴白宮的閣員要抱持希望,劇情有許多高潮起伏。
音樂劇以女主角的獨唱開幕。劇中有許多獨唱的部分,我擔心自己無法勝任,但既然有這個機會,我想要完美的詮釋她,所以很努力投入練習。
正式上演當天小音樂廳幾乎坐滿了人,也有很多朋友跑來看我。
開幕的瞬間,
「該不會在附近的城鎮,爸爸和媽媽就在那邊~」
我氣勢十足開口歌唱,但從中間開始,有幾句獨唱的歌詞我忘得一乾二淨。明明都這麼努力練習了……我現在也會這麼想「原來腦袋空白就是指這回事」,真的就是那種感覺。我慌忙想掩飾,大概連觀眾都替我冒冷汗了吧。看來平常不太緊張的我,當時似乎很緊張。
與母親到小劇場
我會熱衷於舞台表演大概是受到母親的影響。
母親在婚後積極從事保育員、接線生、遺跡挖掘調查等工作,還打零工協助家計,生下哥哥、我和弟弟三人後,她開始投入舞台的世界。她似乎原本就很喜歡舞台劇,因為想試著自己表演,所以加入了一個小劇團,在那裡透過演技練習和舞台活動,得知「竟有如此有趣的世界」,後來逐漸迷上了舞台活動。
每天工作結束,回家準備好家人的晚餐後,母親會趕著出門參加晚上七點的練習。劇團的其他成員白天也各自有工作,只有晚上才能大家一起練習。母親在午夜十二點過後才回家也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小時候因為母親回家太晚我已經睡了,所以會和母親進行交換日記,報告當天晚上的狀況。
我記得在演戲的母親看起來非常開心。
一九八〇年代是小劇場戲劇的繁華時代。母親也是熱衷於小劇場風潮的人之一。母親感受到舞台劇世界的美好,所以也想讓我體驗一下吧。
上小學後,她每週都會帶我去看舞台劇,多的時候可能去看兩三齣。大多是去看「劇團青鳥」、「夢之遊眠社」或「劇團黑帳棚」等劇團在小劇場表演的舞台劇。
小劇場會讓演員和觀眾有連帶感,對小朋友來說就算劇本太難懂也不會在意。舞台和觀眾一同歡笑和哭泣,我非常喜歡小劇場的氣氛。
劇團青鳥的戲劇《仙杜瑞拉……在米糠醬裡打一根釘子》中,所有演員都是女性。這部作品透過從公寓消失的哲子,以及尋找她友人考子的旅行,詢問你在平凡的日常中等待、追求和持續尋找某種東西的意義。裡頭有許多帶有哲學感的台詞,但搭配時髦亮麗服裝或舞蹈會讓人看不膩,那種被帶入虛構世界的感覺,讓我從頭興奮到尾。
我幾乎沒有和哥哥或弟弟一起看舞台劇的記憶,所以母親似乎只想讓我邁入舞台劇的道路。
母親常對我說:「沒有比舞台更有趣的東西了,要是我早點注意到就好了。」
說句題外話,奇妙的是我那沒被帶去到處看劇的弟弟,後來不僅加入了劇團四季,還跳出來自己成立劇團,目前在參與各種舞台的腳本或演出。
小劇場這類麻雀雖小,五臟六腑俱全的會場,會讓我切身感受到緊迫感或熱情。一同流汗,在流淚的同時親身感受舞台魅力之際,我自己也對在舞台上表演抱持強烈的憧憬。
當時有一部少女漫畫叫《玻璃假面》是以舞台劇為主題,在當時已經是暢銷作品,我也曾經迷上過,所以很自然在畢業文集中也點綴了未來的夢想。
遇到一本書決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就讀當地的國立東京學藝大學附屬大泉小學,國中升上同系列的東京學藝大學附屬大泉中學。
我對演舞台劇的心願益發強烈,國二時甚至以特待生的名額加入了演藝事務所「俳協」(東京俳優生活協同組合)。因為這樣,當時大多數朋友都以為我會邁入舞台之路。
另一方面,有個全新的邂逅一直在等待已經上國中一陣子的我。
「衣塑子,妳看一下這本書吧。」
某次,母親不經意拿了一本書給我,那是在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那本名為《南非種族隔離共和國》(一九八九年大月書店)的書本,讓我說不出話來,整個人被吸引了。內容是日本攝影記者吉田瑠衣子(YOSHIDA ruiko)用照片和文章傳達依法推動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共和國日常景象。那時候我知道有種族隔離。但對過著和平生活的我來說,當地「計程車僅限白人搭乘」或「喝水的地方也會分開」的實態已經超乎我的想像。
內容透過照片與鮮明且平淡卻帶有強烈憤怒的文章,介紹了在遙遠的異國之地,黑人的身分不如白人,甚至不被當成人對待的狀況。
南非在二戰結束後不久,人種的差別對待就一直持續。母親也受到很大的衝擊,所以才會推薦這本書給我。
「不要只關心自己周遭,也要時常關心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
這句話母親很少說出口,但抱著這種想法的她,常會推薦我一些說明世界的貧困或不平等的書籍或電視節目。看了吉田瑠衣子的書後,讓我更想認識吉田這個人。
吉田瑠衣子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歷經NHK職員與朝日放送播報員的工作後到美國的知名大學留學。之後居住在紐約十年,期間磨練攝影技巧,在紐約哈林區拍攝的照片獲得高度的評價,並獲得公共廣告獎。
她也是首位進入南非共和國的日本籍攝影記者。透過照片傳達眼前的真實情況,這樣的身影讓我感到正氣凜然和帥氣,也不由得感覺到她那股「必須將這個現實傳達給現在的日本」的決心與使命感。
母親知道我在吉田記者的書上受到超乎想像的衝擊後,也幫我調查了許多事情。
某次,母親不知從哪得到一個資訊,說吉田記者要招待受種族隔離之苦的孩童來日本,並在東京都內主辦音樂劇。我和母親立刻到澀谷的劇場觀劇。
音樂劇結束後,吉田記者走到了觀眾席和觀眾聊天,母親看到後牽著我的手到她的身邊去。
她是什麼樣的人呢……我心跳加速與她近距離接觸,我第一印象是對她嬌小的身形感到訝異。我也算很嬌小,她也和我一樣,可能還比我嬌小一點吧。但她身上卻綻放著一股能量。
我興奮地與她握手,右手傳來某種讓人發麻的東西。如果我也能從事像吉田記者一樣的工作,走遍世界,傳達社會的矛盾和困苦蒼生的真實樣貌,過著她這樣的生活方式就好了——不知不覺間,我開始對此抱持憧憬。
當然舞台劇也很開心。但相較於透過飾演角色去傳達某種事情,我逐漸萌生一種心情,想從事能正視種族隔離等現實發生的事情,並將其傳達出去的工作。有一部份的原因是我從小學就開始演舞台劇,內心某處開始對飾演角色感到些許厭倦了。
在這段過程中,我迎接了高中升學的時期。第一志願是同系列的東京學藝大學附屬高中。就算是同系列的國中,也必須考試才能升上去,這是因為一個學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才升得上去。總之我拼命準備考試,最後成功升了上去。
入學後,我馬上面臨一個選擇。
如果要正式在「俳協」進行包含舞台演員或連續劇等活動,那就必須要限制放學後的活動。我思考了很多,最後決定退出「俳協」。對方讓我當了特待生,所以這是一個難受的決定,但決定之後我就不再猶豫了。因為在嚴厲的升學考試後,我想要享受高中生活,同時也希望未來能變成像吉田記者那樣跑遍世界的新聞記者,這樣的想法在我心中逐漸增大。
來自記者父親的一句話
父親說的一句話也用力推了我一把。父親除了喝酒的時候以外,平常很沉默寡言。小孩想做什麼他都不會干涉,從小到大不管我做什麼,他都會靜靜在一旁觀察,然後在背後幫我加油。
父親身為業界報紙的記者,累積了很長的一段經歷,但後面我才知道他是幾經波折才就任記者這份工作。父親以優秀的成績升上東京都立的升學高中,卻跟大學生一起熱衷於學運。我跟職場前輩或同僚說這件事情後,他們都說「真不愧是妳的父親」。父親似乎度過了熱血沸騰的學生時代,在學期間幾乎沒有讀書。
後來在大學考試備取考上私立大學,但聽到備取要另外繳十萬日圓的入學金後,父親暴怒當場撕掉文件。後來對拍照技巧毫無自信的他,不知為何跑去讀攝影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裡頭,包含電影導演崔洋一在內,有許多性格鮮明的同學。一群晚年和父親也有來往的同班同學,常常稱呼父親叫「洗太淡」。
「以前那個時代我們要自己洗照片,我總是洗得太淡,從來沒有洗好過,所以大家才會這樣叫我。」
父親笑著跟我說。畢業後他曾立志當攝影師,但或許是發現自己沒有才能,所以不久便換了工作。
父親是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聽說是外出旅遊搭船時認識了大他一歲的母親。母親高中畢業後在一間小出版社工作,幾年後她離職了,原因是想外出旅行,搭順風車橫越日本。她在某處搭船時,偶然在船上遇到了父親。
這偶然的邂逅成為契機,兩人結婚了。但該說他們是關係好到會吵架嗎,兩人都是脾氣暴躁的類型,所以從小就常看到兩人因為大小事而激烈爭吵。
這樣的父親第一次回顧自身工作,並和我闡述他的經驗,應該是在我國中或高中的時候吧。
「一直以來,我從各種立場的中小企業經營人或第一線的人那裡,聽到許多事情並寫成報導。雖然我的工作是業界報紙,但感覺就像是站在中小企業的角度看整個社會,這也蠻有趣的。」
父親雖然不像吉田瑠衣子那樣在世界各地到處跑,但還是對記者這份工作抱持肯定的想法,這更加強化了我心中萌生的憧憬。
追尋吉田瑠衣子的腳步
我抱著「想當新聞記者」的念頭迎來大學學測的季節。國中生高中時,我從早到晚都在讀書,但生大學時我就沒準備得這麼賣力,幸好學校的在校成績與日常表現優異,所以我靠推薦上了慶應義塾大學。
上的是法學部政治學科,剛好和我憧憬的吉田記者一樣的科系,成為她的直系學妹。在畢業工作前,我要通過大學內的選拔,跟吉田記者一樣到國外留學——我懷抱這樣的夢想,正式成為一名大學生。
然而,現實卻沒這麼容易。
大概是沒有認真準備大學學測的報應吧。我的英文跟周圍相比落後了一大截。口語表達和聽力幾乎都不行。慶應的留學要先通過學校內的選拔考試。這樣下去留學根本是白日夢。當我抱著一種近乎急躁的心情時,恰好遇見了社團「K.E.S.S」。
正式名稱是「慶映義塾大學英語會(Keio English Seaking Society)」,取縮寫稱為「K﹒E.S.S」。
這個社團以大學創辦人福澤諭吉的兒子福澤一太郎為名譽會長,創立於一八九三年,是歷史超過一世紀的社團。
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文,用英文簡報或演講,這樣不僅能享受社團活動,還能同步提升英語能力,可說是一石二鳥——。
社團內有許多集會,但因為我在入社團前曾經在戲劇集會的甄選會上露臉演出,所以一進社團就被安排到戲劇集會去。光是戲劇集會就有接近一百名社員。其中演員有十人左右。裡頭還有小道具負責人或照明負責人等,雖說是社團卻有十分正規的體制,而我則成了演員。在新的團體用英文塑造角色,這讓我感到很有趣。
這不單只是愉快而已。戲劇集會最大的目標是磨練表現力。
第一年表演的戲劇《仙杜瑞拉的華爾滋》,是世界知名童話《睡美人》的喜劇版,我所扮演的是壞心且瘋狂的繼母。我過去有戲劇經驗,還受過多名舞台導演的鍛鍊,所以有一定的表現力,但我不認為這對提升英文能力會有幫助。
附帶一題,扮演讓女王穿鞋的人是明治天皇的玄孫,跟我同期就讀法學部的竹田恒泰。現在來看,我感覺雙方在思想上是對立的,但他把我當成同伴,甚至有邀請我參加他的婚禮。
對TOEFL成績感到愕然
雖然我的英文幾乎沒有進步,但升上二年級後,我更加渴望到國外留學。因為我得知就算畢業後如願成為一名記者,假如是報社記者就必須在國內累積十年的經歷,才能到海外的分社任職。
於是我才會想趁大學的時候體驗海外生活,增廣自己的見聞。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嚮往曾在美國讀書,並在紐約生活過的吉田記者。
我馬上去考了校內選拔的評估基準TOEFL……但看到分數後我傻眼了。要合格必須要考五百五十分以上,但我只有四百五十分,聽說這個分數代表無法測出你的能力在哪的意思。
這樣要通過校內選拔到國外留學根本就是作白日夢。我因為推薦考上大學而鬆懈,沒有努力學習英文,這讓我感到懊悔。
我這一年到底在做什麼呢,這讓我不得不承認還是應該認真學習才行。
當我這麼想時,公演後有段時間沒往來的「K﹒E.S.S」突然電話聯絡我,希望我再去參加戲劇集會的活動。雖然機會難得,但我還是拒絕了。因為我決定認真學習英文。這種感覺就像遲來的學測一樣。
我覺得自己最弱的地方是聽力。
當時別說是光纖電視,就連網路都沒現在發達。我在大學的課程結束,回到家裡會狂聽三到四小時的收音機。頻道是AM廣播八一〇千赫的「FEN(Far East Network=遠東廣播電台)」,這是專門為美軍基地相關人員和其家屬提供節目的電台,我利用它記住母語人士的發音。
這個電台現已更名為「AFN(American Forces Network=美軍廣播電台)」,廣播主持界的第一把交椅小林克也在小學時也是忠實聽眾,我曾在他的著作中讀到這件事。
剛開始我感覺從喇叭放出的英文就像雜音一樣,明明是一個一個的單字,我聽起來就像黏在一起。內容我也幾乎是鴨子聽雷。這樣真的能提升英文聽力嗎……有好幾次我都想放棄。
然而過了一年後,就在第二年初我終於能掌握到單字的排列。連帶的我的TOEFL分數也變好了,大三時分數總算突破了五百五十分,成功通過大四春天舉辦的校內選拔。
但這不代表馬上就能留學,大約一年後我才終於能出發離開日本。當時是人稱就職冰河期的時代。同學都在拼命進行就職活動時,我老早就選擇留級。當朋友都畢業變成社會新鮮人的一九八八年四月,我出發前往南半球的澳洲。
在留學地受重傷
我挑選的留學地點是慶應的海外合作學校:墨爾本大學。大學的四周被大自然圍繞,校園佔地廣大,城內有路面電車和林立的教堂。這正是有海外大學的感覺,會讓人聯想到西洋的街景。
終於要開始在海外生活!或許是這樣讓我有點興奮過頭了。我剛到澳洲立刻就引發了騷動。
首先,留學生專用的國際宿舍附近有一個網球場,我在那裡用力活動身體,結果扭傷了腳踝。雖然只是扭傷,但我的傷勢頗為嚴重,不得已撐了一個星期的拐杖。
接著,我在某個派對上抽中可縱橫澳洲大陸的旅遊券,於是我興高采烈地前往澳洲北部的達爾文,結果在那裡頭部受了重傷。
澳洲最北邊的達爾文有一個能從石頭上跳水的湖泊,也是熱門的觀光景點。
我到那裡時,有一個德國觀光客從十公尺高的地方歡呼一聲跳入湖中。因為實在很可怕,所以我從五公尺的地方開始挑戰……結果跳下去之前,我腳滑了一下倒栽蔥摔落湖中,一頭撞上了湖泊前方的岩石。
我在摔落的瞬間,好像事不關己一樣萌生了「啊,我可能會這樣就死掉」的想法,頭部撞上岩石的瞬間,我感覺非常刺痛。用手摸頭後,發現頭上有黏糊糊的鮮血。周圍的人發現到這個慘況,合力將我抬出湖泊。
我額頭右側,剛好在髮際一帶受了撕裂傷,被運到醫院縫了幾針。醫生甚至要我住院兩週。我的脖子被石膏牢牢固定,必須在病床上絕對靜養。醫生對我這麼說:
「妳很幸運呢,好險脊椎沒有受傷。」
這個摔落事故變成了一大騷動,甚至上了達爾文的地方報紙。
「妳回來的時候可要擺脫拐杖啊。」
我出發前,宿舍的大家用這句話送我離開。現在回想起來,撐著拐杖去旅行,還想跳水入湖的我也實在是很厲害。
我因傷比預期還早回到宿舍,頭上包著繃帶,脖子打了石膏。看到我悲慘的模樣,出來迎接我的大家開口關心的同時,也按耐不住捧腹大笑。
這個傷痕現在還在,平常我是用頭髮遮住,但依不同的角度,看起來會像圓形脫毛症。
偶然看到我頭上疤痕的同僚或記者朋友,都會用一本正經的表情同情我說:
「望月……妳真的很操勞呢。」
「雖然妳平常那樣,但其實內心很纖細呢,別太勉強自己啊。」
今年對我這樣說的人一口氣增加了,但我說明原委後,他們就會改口笑著說「這果然有妳的風格呢」。
在大學的專題研究感受到核威懾理論的「陽剛感」
我原本想在墨爾本大學學習女性主義。
我在慶應時,從三年級的九月開始就隸屬於「赤木完爾研究會」。原本專題研究是從三年級的四月開始,但因為法學部的赤木完爾副教授(現為教授)當時在海外留學,所以才會從九月開始。
對拼命準備海外留學的我來說,這多出來的半年我可以拿來提升TOEFL的成績和學習英文, 於是我選擇加入「赤木完爾研究會」。
然而,由於赤木副教授曾在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擔任戰史部教官,所以課程中的討論都圍繞在現代國際政治或安全保證研究,感覺非常「陽剛」。
特別是安全保證研究的基本思維是核威懾理論,要有某種程度的武力或軍事力,國家之間才能保持平衡。甚至有專題研究班的學生,還去參加防衛廳在暑假為一般社會大眾舉辦的軍事訓練。
我對過去曾投入學生運動的父親有些抗拒,一直覺得自己「沒有父親那般偏頗」,但我和立場完全相反的「赤木完爾研究會」卻無法有思想上的共鳴。
雖然我說了一堆,但其實我的本質還是跟父親相似吧。當我在思考自己的立場時,覺得有點無法贊同課程的內容。當大多數人的畢業論文都選擇安全保障類的題目時,課業有些落後的我刻意選擇了「印度的教育政策」當題目。
因為有這樣的反作用力,所以我在出發到澳洲前,就一直對女性主義、女性學和性別學感興趣。
順理成章地我在墨爾本大學也參加了女性主義研究會,但是情況明顯和日本不一樣。全球的女性聚集在一塊,氣氛非常熱烈,彷彿在討論戰鬥的學問一樣,這種被氣場壓倒的感覺,我現在依舊歷歷在目。
接近回國的時間時,當然畢業後的事情也會在腦中浮現。有一陣子我曾想過升上研究所繼續進行女性主義的研究,但到了一九九九年初,我開始有強烈的意念,想早日踏出身為新聞記者的第一步,因為這是我從高中時代就一直懷抱的夢想。
我的學生宿舍被大自然圍繞,是一個很悠閒的地方。學習和跟夥伴之間的情誼等,我經歷了一段很棒的時光,但一到晚上九點周圍就會被黑暗圍繞,這也開始讓我感受到有所不足。
這可能是因為我生長在喧鬧的東京——這個人潮絡繹不絕,有無數資訊交錯,霓虹燈永遠不會消失的城市吧。
回到日本之後,要努力找工作才行,我抱著這樣的想法回國了。
求職的筆試成績全軍覆沒……
春天回國後,我到報社或電視台拜訪了大學畢業的學長姊。
當時手機和電子郵件不像現在這麼普及,所以我是臨時打電話給對方。幾乎所有的學長姊都在百忙之中抽空和我見面。
當時已經是每日新聞社的堂姐:望月麻紀也是我商量的對象之一。當時她第二次外派到分局,剛在博多經歷完每天取材的日子,又接到了調往政治部的人事異動,人才剛回到東京不久,當時她說了這麼一句話:
「真希望上面馬上把我調回博多呢。」
她在博多負責採訪警察單位,當然也會有辛苦的地方,但是真的是一份有趣的工作,她語帶熱誠地這麼說到。我對新聞記者,特別是對報社記者的憧憬變得益發強烈了。
同時我也想嘗試自己來採訪看看。於是我決定到東京一個叫山谷的城鎮。橫跨台東區與荒川區的山谷地區,是日領臨時工的聚集地。我到那裡採訪了當地居民。
一個人走在路上,我也不覺得可怕。當我一路傾聽各種聲音後,所感受到的是當地人心中的寂寞。
他們說自己也有一些問題,所以才會被逼入現在的窘境。有些人傾訴說想見四散的家人,也有人聊了自己的小孩,看似十分想念他們。
國家或行政單位是否能夠幫助他們呢。我記得當時邁入大學六年級的我,心中朦朧浮現了這樣的想法。
接著,我展開了就職活動。願意和我見面的學長姊都異口同聲地給了我這樣的建議:
「妳的性格非常好,所以面試不會有問題。只要通過前面的筆試就一切OK了。」
然而,現實沒有這麼容易。等待我的是連戰連敗的每一天。
大眾媒體的就職考試是從全國性的大型報社開始。我在讀賣新聞社、朝日新聞社、日本經濟新聞社的第一階段筆試被刷掉,無法進到第二階段面試。NHK雖然通過第一階段的面試,但在第二階段的筆試被刷了下來。
雖然大型媒體落榜了,但我沒有時間沮喪,再來是地方的跨縣報社。
大型報社都沒上的確讓我很震驚,但我聽說只要在地方報紙努力當記者,未來被全國性報社挖角是很常見的事情。身為記者老前輩的父親也常對我說:
「大型媒體落榜了也不用太氣餒。他們的入取率本來就很低啊,有考上其他報社就好了。」
我同一時間也去考了民營電視台,通過了日本電視台和富士電視台的筆試後,到了後續的面試,我說明自己的報考動機是想從事報導工作,他們理所當然地回應說:
「電視台的話,大多會被分配到業務或製作的工作。如果想從事報導的話,可能無法貫徹妳的初衷喔。真的想從事報導工作的話,要不要考慮去報社?」
於是兩家電視台都在最終面試前落榜,我感受到同樣是報導,但報社和電視台的氣氛似乎有點不同。這是我在今年出席菅義偉內閣官房長官的記者會後,無意間回想到的事情。
跨縣報紙中,北海道新聞與東京新聞的徵才比較早。東京新聞正確來說是由中日新聞社東京本社發行的關東地區及東京都的跨縣報紙,但也會刊載全國性的新聞。
我接連通過北海道新聞和東京新聞的筆試,後者經過東京本社的面試後,到了中日新聞社的本社所在地愛知縣名古屋市進行最終面試。接著,北海道新聞的最終面試結束,當我在等待合格通知時,東京新聞通知我已經被內定了。
這個瞬間,我的就職活動也宣告結束。我向尚未公布結果的北海道新聞說,自己將會去中日新聞。
在新人培訓階段配送報紙
到了二〇〇〇年四月,我比同期進大學的人晚了兩年進入了社會,進入了中日新聞社東京本社,步上我一直憧憬的新聞記者之路。
不過就跟一般企業一樣,報社也有新進員工培訓。當時我在中日新聞名古屋本社培訓了五個月左右,在社會部、運動部、寫真部等擔任實習生,學習報導的撰寫方式或照片的拍攝方法等基礎技巧。
培訓中最特別的是實際配送報紙。我在愛知縣內的中日新聞專賣店住宿了一個月,體驗把剛印好的報紙送到訂戶手中的各種過程。
報紙從印刷廠印好送來後,新人要在每份報紙夾傳單,然後搬到摩托車或腳踏車上 到負責的地區配送,風雨無阻。要抱著感謝的心情,準時將報紙送達等待報紙的讀者手中。
但這個新人培訓的工作方式,會依被分配到的專賣店而各不相同。我分配到的地方是春日井市內的專賣店,經營者是一對溫柔的初老夫婦。
當時我只負責晚報的部分,他們幫我準備了一間整潔的房間和床鋪。房間本來是他們的小孩在使用,現在小孩已經離家獨立生活。每天太太會親手幫我準備三餐。快五月底的時候,我的體重也稍微增加了。
培訓結束後,我再見到同時期進公司的夥伴,大部分的男性員工都暴瘦了一圈。聽說他們每天都要送早報和晚報,甚至有人是跟其他人同房,不分晝夜被徹底操了幾個月。
聽到我的待遇後,他們異口同聲地羨慕說:「不敢相信,居然只要送晚報!」
八月下旬結束培訓後,我的工作崗位決定了。
我被分配到千葉支局。搬好家之後,我滿心期待,帶著興奮到近乎發抖的心情進入了支局。但沒想到,我不久後居然會在採訪地點嚎啕大哭。
馬上後悔當記者
事情發生在二〇〇〇年九月一日下午,晚報剛截稿不久後。一名前報紙銷售所的業務因為殺害同居養母,並棄屍在千葉縣鋸南町的鋸山中而被捕,後因為對其他女性女性施暴而被四街道署的搜查本部再次逮捕。
組長下令我去採訪住在四街道市內的死者家屬,請他們針對犯嫌被捕一事做出評論。
我急忙開著支局的車子,一個人趕往了現場。但我對當地完全不熟,那時當然不會有導航,一邊開車也不方便一邊看地圖。原本只要三十分鐘就能到的地方,我迷路了接近兩個小時還沒到。
後來我找到公共電話,打了電話回支局。
「妳現在到底在哪裡!人還沒到嗎!」
就算你這麼說,我已經很拼命在開車了,我把這個心情藏在心裡,好不容易抵達了目的地。
其他公司的記者已經走光了。大家都採訪完回支局了吧。
終於趕到的我,急忙跑上公寓的樓梯,來到死者家屬的住家面前按下門鈴。死者高齡的妹妹打開了門。我報上報社名稱和姓名,戰戰兢兢地說出了自己的目的後,她的先生走過來擠出了這句話:
「請放過我們吧。我們無話可說。」
他的聲音有氣無力。或許已經有好幾家報社來按過門鈴。那是一種悲傷又無奈的聲音。
我沒辦法繼續發問,因為對方的心情湧入了我的心中。
我回到車上,在一段距離外找到公共電話並打回支局。
「這種狀況實在太可憐了,我問不下去。」
我直接說出自己的心情,但話筒另一端的語氣卻非常冷靜。
「不行,妳再去問一次!」
當時的時間逼近傍晚,但天氣還是很炎熱,忙碌的蟬叫聲在四周迴盪。
我掛掉電話,帶著沉重的步伐回到車內,用力甩上車門,眼淚不斷湧出。
這起事件的男性犯嫌,在一九九八年成為被害人的養子。雙方是經由共通的友人介紹認識,被害人大他一輪。兩人同住在四街道市內,後來男性因為負債超過一千萬日圓而被責罵,一怒之下勒住了被害人的脖子,還用石頭毆打其頭部致死,並棄屍在鋸山山中的灌木叢。遺體被發現時已經成了白骨。
在之後的審判中,我得知被害人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我為什麼必須要被殺死」——被害人的悔恨讓我感到鬱悶。此時,我還不知道這句話,但為了讓讀者明白被害人的感受,上面交代死者家屬的評論不能只是「請放過我們吧。我們無話可說」。我想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一方面,對方已經很悲傷了,為什麼我還要做出傷害他們的殘酷行為,詢問會讓他們感到厭惡的事情呢,這種無處宣洩的心情同樣湧上了心頭。
現在的我如果看到了,大概會說「等一下,為什麼妳會因為那種事情而哭啊。」但當時只是菜鳥的我,覺得我一直嚮往的新聞記者這份工作,跟我被指派的任務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內心感到十分愕然。
沒人看得見,聲音幾乎不會外露的車內,是最適合哭泣的地點。過了不久,我的淚水也跟著收斂,心情稍微平復了下來。
直到此刻我才覺得「我怎麼會選這份工作呢」,同時我也心念一轉,覺得「頭都已經洗一半了,只能繼續做下去」。
「如果無法放上評論,就無法傳達死者家屬的遺憾。」
對記者這份工作的死心、絕望和使命感同時交錯,成了我當下的心情。
距離第一次造訪大概三十分鐘過後吧。
我再次按下了門鈴。前輩記者曾經教過我,在對方開門的瞬間要用腳尖把門擋住,不要讓對方把門關上,但當時我實在做不到。我下定決心,再次表明來意。
或許是他們可憐滿臉歉意再次來訪的菜鳥記者吧,願意簡短接受採訪的死者家屬,留下了一句話給我,內容大概是「死者不會因為這樣就死而復生,但是看到犯人被捕讓我們鬆了一口氣」。
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我拼命用原子筆做筆記,然後打電話向組長報告。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字數或版面,但這段評論被刊載在隔天的早報上。
「這就是記者的工作啊。」
我的腦中浮現受訪的死者妹妹夫妻,心中的某處感到釋懷了。
作者資料
望月衣塑子
1975年生於東京都。東京新聞社會部記者。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畢業後,進入東京中日新聞。主要採訪的對象為千葉、神奈川和埼玉的各縣警、東京地檢特搜部等。2004年獨家報導日本齒科醫師聯盟涉嫌非法政治獻金,踢爆自民黨與醫療業界的權力結構。而後負責採訪東京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的審判案件,接著又以經濟部記者、社會部機動記者的身分,採訪了防衛省的武器出口,以及軍方與大學的共同研發等主題。2017年4月之後,成為森友與加計學園問題的取材團隊一員,同時在官房長官記者會上持續提問。 著作有《武器輸出と日本企業(武器出口與日本企業)》(角川新書)、《武器輸出大国ニッポンでいいのか(日本真要變成武器出口大國嗎)》(あけび書房,共同著作)。育有一對子女。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