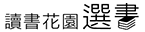暗房裡的男人:變性者一生的逃逸計畫,一場父女的和解之旅。
- 作者: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
- 出版社:網路與書出版
- 出版日期:2017-11-02
- 定價:500元
-
購買電子書,由此去!
本書適用活動
內容簡介
*2016年科克斯文學獎
*2016 年《紐約時報書評》年度好書
*2017年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入圍
*七十六歲家暴父變性,一個女性主義者如何揭開他/她的身分之謎?
*大半生在暗房裡修圖的男人,在性別、政治、宗教、國族認同上一直掙扎、塗改修飾。身分認同是你選擇的,還是你無法逃避的?
*已售出美、英、法、德、匈、義、荷、西班牙、瑞典語言版權
「我在追逐一名罪犯,一名技藝精湛的逃脫者,這名逃脫者從許許多多重要事物中缺席:責任、親情、過失、悔恨⋯⋯在我們的合作關係裡,多數時間都恍如貓捉老鼠的遊戲,一場通常由老鼠贏得最後勝利的比賽。」
二○○四年,蘇珊.法露迪收到一封主旨為「一些改變」的電子郵件,寄信人是史蒂芬.法露迪——一個二十五年來和她幾乎沒有說過話的父親。「親愛的蘇珊,我有一項有趣的消息要告訴你。我決定了,我受夠了老是扮演一個自己內在從來不是的、好勇鬥狠的大男人。」七十六歲的史蒂芬向女兒宣告自己變性成為一個女人:「史蒂芬妮進入真實世界了!」
在蘇珊的成長過程中,父親一直扮演殘忍的暴君角色,燃燒起她早期的女性主義思維。這位暴躁的男子漢,為什麼要變性?當她逐步抽絲剖繭父親變性背後的原因時,她發現箇中超越了性別認同的議題,還攙雜父親作為二戰時期匈牙利的猶太倖存者,經歷國家、種族、政治、宗教等複雜的身分認同問題——毫無預警地走入了一個黑暗的歷史迷宮。
這位半生躲在暗房裡修圖、切割拼貼的男人,一生也在處心積慮改造自己的身分。史蒂芬試圖從一名內心痛苦的兒子、處境艱難的丈夫和父親的憂愁歷史中抽身與人隔絕,而史蒂芬妮決定要打開暗房的門走到鏡頭前,邀請曾離棄她的女兒進入她過去的世界,去寫下她的故事。
這是一部關於失落的愛與和解的家族回憶錄,也是有關大屠殺中猶太人的歷史,更是一本探討身分變換、叩問真我的作品。
【媒體讚譽】
《暗房裡的男人》是一本絕妙精彩的回憶錄——犀利、冷靜,在令人意料之處感動萬分。法露迪女士決心揭開她青春時父親的神祕面紗——「他是一個既神祕莫測又暴躁失控的存在;像個黑盒子,也像顆不定時炸彈」,同時重新檢驗身分的概念與本質。
——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法露迪是一位冷面笑匠和謹慎的作家。她沒有這些時日的回憶錄中偽裝為洞見和力量,實為不可自制的濫情與自戀⋯⋯然而,當我讀她的書時經常哭泣,且一度不得不放下書本,放空一下情緒。
——瑞奇.庫克(Rachel Cooke),《衛報》(The Guardian)
在這本引人入勝的書中,作者處理了一個相當複雜的主題,法露迪女士⋯⋯相當出色地追蹤著她擁有多重矛盾身分的父親的真相⋯⋯像是偵探小說的情節般展開她父親的故事。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令人感動⋯⋯《暗房裡的男人》是法露迪渴望了解她爸爸的悲傷的情感上的追尋⋯⋯法露迪在尋找身分複雜的、一輩子的、千變萬化的脈絡中,展現她父親的手術。
——《新聞周刊》(Newsweek)
法露迪文思敏捷、及時的、影響深遠而私密的新書⋯⋯混合了家庭祕密、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女性主義、暴力、大屠殺、報復的文類和主題。將其交織的是身分的問題:誰,或什麼,造就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是什麼?以及最終的結果多麼牢不可變?
——《她》(Elle)
最終這本書是一場愛的行動⋯⋯一場耗費十年,試圖理解一位始終不屈不撓的親人的迷人記事。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卓越非凡:一部分是饒富興味的家族回憶錄,一部分揭露了大屠殺的歷史,但最重要的是對人類身分的深刻省思⋯⋯《暗房裡的男人》來得正是時候。這也是高度重要的一本書⋯⋯我們活在一個為了身分苦戰不休的年代——卻少有人如蘇珊.法露迪般有著想去了解的仁慈欲望。
——《國家書評》(The National Book Review)
法露迪獻給她已故父親一項很好的禮物,在這樣一個令人信服、真實的故事中,讓父親的人生躍然紙面。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目錄
序曲:追捕父親
第一部
1 歸來與離開
2 後窗
3 複本的正本
4 居家不安
5 你原本應該成為的人
6 這不再是我了
7 他的身體碎成片片。她的身體。
8 家鄉的祭壇上
9 拉道伊街九號
第二部
10 更多的與其他的
11 無論任何情況,一位淑女就是一位淑女
12 思想是個黑盒子
13 學習遺忘
14 某種心理上的不安
15 皇家大飯店
16 被上帝打退的猶太人
17 適應的慢性毒藥
18 你走出森林
19 病患的轉變是無庸置疑的
第三部
20 喔,神啊,憐憫,匈牙利人
21 一切女性的舞步
22 償清
23 僥倖逃脫
24 孕育世界的日子
25 逃脫
序跋
序曲
追捕父親
二○○四年夏天,我像一名警探,著手調查一位我幾乎一無所知的人物,我的父親。身為女兒,父親卻從自己生命中潛逃,我是以一種悲傷的心情展開這項計畫。我在追逐一名罪犯,一名技藝精湛的逃脫者,這名逃脫者從許許多多重要事物中缺席:責任、親情、過失、悔恨。我準備起訴他,將所發現的一切累積成一項控訴。但在過程中的某個時刻,控訴者變成了見證者。
我所見證的則始終令我難以理解。一生當中父親克服萬難,成功實行了如此多項的改造計畫,他宣稱自己擁有各種不同的身分。「我是一位匈『押』利人,」不管身分如何多變,父親以始終如一的口音在吹噓著。「我知道如何『鱉』故事。」如果事情真有那麼簡單就好了。
「寫我的故事,」父親在二○○四年對我提出一項邀請——或者,該說,對我下了這紙戰書。邀請的目的並不明確。「這本書可以像安徒生童話一樣。」後來有一次,父親對我說明我們的傳記事業:「安徒生寫的童話故事,裡面所有情節都是真實的,他只是用魔幻把它包裝起來。」這不是我的寫作風格。然而,出於報復的心情我接下戰帖,內心則有我自己的盤算。
儘管開啟了這個序幕,但父親始終是個執拗的寫作對象。在我們的合作關係裡,多數時間都恍如貓捉老鼠的遊戲,一場通常由老鼠贏得最後勝利的比賽。父親很像另一位同是匈牙利人的逃脫大師胡迪尼(Harry Houdini)。至於我——我的角色設定為持續追捕,直到將他緝捕到案的一人警衛隊——跟蹤父親的許多分身,直搗他們的祕密藏身處。原本我的目的是要寫關於父親的故事,直到二○一五年的夏天,在完成好幾回草稿,繳交初稿,面對父親過世之後,我才意識到這本書同時也是為了父親而寫。至少在我心目中,父親已成為我的頭號讀者,也是我所想像的、內心預設的讀者——殊不知這句話同時暗藏了多少的寬大為懷與惡意算計。這並不是一份簡單的禮物。
「書裡會提到一些令你很難接受的事。」我在二○一四年秋天警告他。我打電話給他宣布我的初稿完成了,我嚴陣以待他的回應。假定父親一輩子在商業攝影領域從事影像修改工作,並且一生處心積慮修改自己的身分,我猜他一定會討厭被描述成一顆瘤般的存在。
「哇歐,」一陣沉默後,我聽見他愉快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我很高興。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一生。」總算有這麼一回( 儘管只是在紙面上)父親對有人捕捉到他而深感心滿意足。內文試閱
1 歸來與離開
一天下午,我在奧瑞岡州波特蘭家中的書房裡工作,將一項之前的寫作計畫,一本關於「男性氣質」的書的成堆筆記放入檔案盒裡。當時我面前的牆上掛著一幅最近剛添購的鑲框黑白照片,照片裡的人物是一位名叫麥爾坎.哈特維爾(Malcolm Hartwell)的前美國軍人。這張照片是一項展覽的一部分,展覽的主題為作「一個男人的意義」(What Is It to Be a Man?)。被拍攝的主角受邀發表影像作品,並附上一句文字說明。照片中的主角哈特維爾是一位身材結實的大漢,他穿著飛行靴與工人褲,在他的道奇雙門轎車前擺出一個向觀者挑逗撩撥的姿勢,一隻手戴著手套,擺在肥大的屁股上,雙腿交叉,一隻腳踝放在另一隻腳踝上。標題的手寫字跡出現沒有被修除,錯得恰到好處的別字:「男人無法連結『那裡』的陰柔氣質(Men can't get in touch with there feminity)。」我暫時從整理檔案盒的工作離開,起身檢查了一下email,發現一段新的訊息:
收件者:蘇珊.法露迪
日期:二○○四年七月七日
主旨:一些改變
寄件人是我的父親。
「親愛的蘇珊,」信件開頭寫著,「我有一項有趣的消息要告訴你。我決定了,我受夠了老是扮演一個自己內在從來不是的、好勇鬥狠的大男人。」
聽到這項消息其實我並不完全感到意外,因為我不是父親宣布其重獲新生的唯一對象。另一名多年沒有見到我父親的家族成員,最近接到一通來自父親的電話,東拉西扯關於自己住院以及去泰國的種種。掛上電話之後,他收到一封令人出乎意料的電子郵件,裡面有一個附檔,打開來是一張父親的照片。照片中的父親站在樹杈之間穿著一件淡藍色上衣,看起來像女性穿的短袖襯衫,領口還有樸素的荷葉邊裝飾。照片的標題是 「史蒂芬妮」(Stefánie)。緊接著父親來電,他的訊息很簡短:「史蒂芬妮進入真實世界了。」
父親給我的電子郵件訊息也類似那般簡潔。但有一件事沒變:我的攝影師父親仍然喜愛影像勝於文字。附加在信件裡的是一系列快照。
在第一張照片裡,父親身穿一件透明的無袖襯衫與紅裙,佇立在醫院的大廳,旁邊站著(如她的註腳所寫)「其他手術後的女孩」——有兩位病人也進行了她稱為「重大改變」的手術。另一位穿制服的泰國護士則挽著父親的手肘,圖說寫著:「手術後我看起來很疲倦。」其餘的照片則是「手術」前拍的。其中一張照片裡,父親在樹蔭下歇息,頂著一頭指甲花色的假髮,蓄著劉海,身上穿著同一件領口有皺褶的淡藍色襯衫,圖說寫著:「維也納花園裡的史蒂芬妮」。這個花園是奧匈帝國女王的皇室度假勝地。長期以來,父親十分擁戴中歐皇室,尤其是別名西西(Sisi)的伊莉莎白(Elisabeth)女皇,她也是奧匈帝國第一位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的妻子,有著匈牙利守護天使的封號。在第三張影像中,父親戴了一頂長度及肩,五○年代大波浪風格的淡金色假髮,上半身是一件白色帶有褶飾邊的女性襯衫,下半身穿著另一件有白百合圖案的紅裙子;腳上穿著一雙白色的有跟涼鞋,露出了塗上指甲油的腳趾頭。在最後一張名為「在奧地利健行」的照片中,父親站在福斯露營車前,腳上穿著登山靴,身穿單寧布裙,頭上戴著內鬈的假髮,脖子上繫了一條波卡圓點圖案的絲巾。他一隻手擺在曲線曼妙的臀部上,穿著絲襪的雙腿交叉,一隻腳踝放在另一隻腳踝上。我抬頭看看牆上照片的標題:「男人無法連結『那裡』的陰柔氣質。」
再看看電子郵件的署名: 「愛你的親人,史蒂芬妮。」這是多年來第一次收到來自我「親人」(parent)的信件。
二十五年來,我和父親幾乎沒說過一句話。小時候我厭惡他,之後,我懼怕他,在我的青少年時期,他離家出走——或者應該說是經過幾個月不斷加劇的暴力行為,被母親與警察強迫驅離。雖然我與父親長期疏離,我自以為了解父親的個性,能足以理解他潛藏的性格深處女性氣質的蛛絲馬跡。結果是我一點也不。
童年時,我們住在距曼哈頓往北一小時車程,約克鎮高地(Yorktown Heights)郊區「殖民風格」的集合式住宅。我所認識的父親始終是男性獨裁的擁戴者。尤其在家庭生活的最後幾年,他堅決地、毫不妥協地、殘忍地投入扮演暴君的角色。我們吃他想吃的食物,去他要去的地方,穿他規定我們穿的衣服。家中無論大大小小的決定,首先都須經過陛下的同意。一天晚上,母親提出想接受一份在地區報社的兼差工作,父親以把桌上餐盤掃落一地的方式,清楚表達了他父權崇拜的觀點:「不准!」他大吼,拳頭砰地一聲擊打在桌面。「不准去工作!」就我回憶所及,他始終是專斷獨行的父系家長,蠻橫又專制;另一面的他則始終是一則待解的密碼,是周圍人眼中的謎樣人物。
我知道在他清瘦的體型下,其實住著一位個性粗獷的戶外生活家:他擅長各類運動,他是登山者、攀岩家、攀冰者、水手、馬師,也是一位長距離的自行車騎士。與他的內在身分相應的服裝包括:登山杖、巴伐利亞健行褲、登山面罩、攀岩安全帶、快艇帽、英國騎士皮褲。在這些運動項目的競逐過程中,我是他的隨行夥伴(雖然踏進青春期後,我對這個角色愈來愈抗拒)。在他用工具組裝的克萊普帆船(Klepper sailboat)上,我是他的船長二副;是在他假日攀登夏文岡 (Shawangunk)懸崖時棄他而去的背叛者;是他橫跨阿爾卑斯單車之旅的第二騎士;在阿迪朗達克(Adirondack)野外營地擔任他搭建帳篷的助理。
參與所有這些運動需要長時間的訓練,長途旅行期間彼此分享親密時刻,但很奇妙的是,我對參與這些歷險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當帳篷已經搭好,木柴都收集完畢,父親用隨身攜帶的瑞士刀撬開罐頭,在那些已無事可做的漫長冬季傍晚,我們究竟聊了些什麼?是我壓抑了那些父女間悄悄話的回憶,還是這些回憶根本不曾發生?年復一年,從莫宏客湖(Lake Mohonk)到盧加諾湖 (Lake Lugano);從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s)到策馬特山脈(Zermatt),我們以圖釘紮營、我們揹背包上路;我們用繩索從懸崖陡壁滑下;我們騎行而過。在所有這些活動的過程當中,我卻無法斷定他有對我真實坦露過。他看起來像永遠活在自己所構築的一道牆後從事某些祕密工作,躲藏在腦內單向透視的玻璃後觀察外界動態。至少對一位渴望隱私的青少年來說,他的窺視是不懷好意的監看。
我有時會把他當成意圖混進我們居家生活的間諜,並盡其可能預備好,迴避他的偵查。然而,在充滿侵略性的支配行為之外,他卻又始終保持一名隱形人的姿態。「就像他從沒在這住過一樣,」在經過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也是父親永遠離家的那晚次日,母親這麼告訴我。
十四歲時,父母分居的兩年前,我加入了學校的田徑初級校隊。一九七三年,「女子運動項目」是一種意義含混不清、相當荒謬的說法。國高中的田徑教練,主要負責男生隊的訓練,他們大都會忽略訓練女生的任務。當時我制定了一套給自己的訓練規範,黎明前離家,在小巷中跑步,一路跑到一個樹木修剪得相當整齊、前身是州立精神病患收容所的休閒風景區——莫漢斯州立公園 (Mohansic State Park)──自個兒繞著偌大的公園跑完一圈。當時我已發展出對單人運動的偏好。
在一個八月初的清晨,我正在前廳門口綁鞋帶,就像冷鋒接近時氣壓計下降,或偏頭痛來臨前事先的刺痛——我那青少年的腦袋瓜偵測到「父親來了」的微弱訊號──我不情願地轉過身,辨認出他蒼白瘦削的骨架,從樓梯轉彎的陰暗角落浮現。他身上穿著運動短褲和網球鞋。
他在樓梯最後一階停了下來,古怪地調整了一下姿勢,像是從鑰匙孔窺探外界般檢查了一下眼前的狀況。過了一會,他說:「我『耶』要跑步,」濃重的匈牙利口音從「也」這個音節拉長。這是一項命令,而非邀請。但是我跑步時不想有人在旁邊。不知從哪冒出的一首打油詩在我腦中縈繞。
昨天,在樓梯間
遇見一個從沒見過的老漢
今天他也同樣沒出現
我希望,我希望他走開不見⋯⋯
我推開紗門,父親的陰影從頭直籠罩到我的腳跟,空氣因溼度而膨脹,我用鞋頭戳了戳柏油路面上突起的瀝青泡泡。父親反覆思考著,他先轉頭看看他的老式福斯露營車,再轉頭望向最近新買的,萊姆綠的二手飛雅特敞篷車,「這車是為你母親買的。」然而母親並不開車。「哇歐,」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們開飛雅特。」
短短五分鐘的路程,車上一片死寂。他開進I B M 研究中心的停車場,距離我們的目的地僅隔一個街區。醒目的標示上清楚註明停車場是員工專用,父親完全忽視這項標示繼續往前開,他一向對自己一些小的犯罪行為( 他稱之為「瞞天過海」) 感到相當驕傲。這項偏好也促使他將當地購物中心的貨價標籤掉包,因此省下二十五塊美金,成功得到一只露營用的飯鍋。
「你的車門有上鎖嗎? 」當我們下車穿越停車場時,父親問我。我回答,有上鎖。他懷疑地看看我,轉身走回停車場檢查。父親這些細瑣的破壞行為的反面,是他對行事安全的極端重視。
我們步行過光禿禿的產業道路,走上二○二公路,這也是沿公園北緣前進的主要道路。我們一路閃避加速的車輛,爬過金屬分隔島,跳到分隔島後方的凹地上。父親暫停了一下。「那件事是在那發生的,」他說。他經常這樣沒頭沒腦的對自己說話,彷彿對話進行到一半地喃喃自語。我了解「那件事」指的是什麼,幾個月前,午夜過後,一群從宴會返家的青少年撞上斯特朗大道(Strang Boulevard)上的停止標誌,接著與另一台車對撞。兩台車都因撞擊飛過分隔島,四輪朝天。這場車禍沒有生還者。一位乘客的頭被輾斷了。我父親沒有目睹車禍發生的經過,但目睹了事件的後續。當晚約克鎮高地救護大隊傳喚他去做志願服務。
父親亟欲擔任當地緊急醫療服務的志工,這不太像他會做的事,至少不是我所認識的他會有的行為。通常他會躲避社區事務及一般性的社交活動。有幾次父母邀請客人到家裡來,父親不是一言不發地坐在搖椅上,就是以投影機為掩護,更換著一盤又一盤之前我們去健行的柯達投影片,他會讀出每張投影片框上每座主峰的名字,並向客人細數沿路彎道的每個細節變化,直到訪客因無聊以致失去耐性,起身告辭,打道回府為止。
他談論醫療救護團的服務,稱之為「我『揪』人性命的工作」。這事我同樣無法理解。我們的小鎮平靜無波,根本沒有事件發生,召喚九一一的都是些郊區緊急求助,如:貓困在樹上下不來,家庭主婦心臟病發作,偶爾一兩起因忘了關爐子釀起的小火災。莫漢斯州立公園的車禍是個例外,並且也沒有人需要救援。當父親抵達車禍現場時,警察正為屍體蓋上白布,救護車的司機抓住父親的手臂,「史蒂芬,別看,」父親回憶司機當時說,「你不會想在記憶裡留下這個畫面。」司機不曉得這殘骸的印象已牢牢嵌入父親的記憶,無論他多麼努力都無法消除。
將之前發生車禍的地點拋諸腦後,我們兩人開始沿著鋪平的道路奔跑,經過一排排空著的停車場,一路跑到露營區。道路起始於棒球場與籃球場所延伸出幽暗平坦的一個空地,然後圍繞著巨型的公共泳池(暑假時我就是在這裡的零食攤位打工)再沿著莫漢斯湖,最後終止在一座很長的山坡上。在湖邊,我們挑選了一條狹窄的步行小徑,兩人不發一語,一前一後地跑著。
最後一段是爬坡,小徑漸成寬闊的路面,因此我們開始肩併肩跑著。幾分鐘後來到上坡路面,他跟上速度,我加速了一些;他再加速,我又再加快速度,他再度領先,然後換我。就這樣,我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我看向他,但他沒有回看我。他紅通通的皮膚上閃爍著涔涔發光的汗珠。他的目光往前直視,聚焦在一條隱形的終點線。一路上坡的過程中,兩人維持熾熱而沉默地算計著。當道路平緩下來,我因疼痛減慢了跑步的速度,感受胃部劇烈的起伏,視力也變得模糊。此時父親突然暴衝邁開大步前進,我試著跟上他的速度。但畢竟那是七○年代初,晨跑時我腦海裡的電影配樂響起了〈我是個女人(聽我怒吼)〉 這首歌。但無論是我對婦女解放運動的狂熱、我的青春或我的訓練,都比不上他的決心。
在那一刻,父親某些部分似乎變得伸手可及,不再遙遠,但是什麼呢? 我見證的是他天生的爭強好鬥,還是只是一場刻意的表演?他在與他的女兒競爭,還是想超越某人某事或其他? 但這些並非那天早晨我腦中所思考的問題,當時我只試著讓自己別嘔吐。但我記得有個念頭,在那場跑步的最後幾分鐘一閃而過,令我初啟蒙的女性主義思維感到困擾,這個念頭是:當女人比較輕鬆。隨著這個想法的出現,我讓自己的雙腿慢下來,父親的背影則一路遠離。
那些年在家的時光,父親是《大眾力學》(Popular Mechanics)雜誌裡那種周末居家男士的典範,永遠都埋頭於最新的居家手工藝計畫:音響電視組合櫃、挑高設計的書櫃、狗屋與圍欄(做給我們的匈牙利小獵犬珍妮〔Jání〕)、短波收音機、兒童攀爬架、一個有著循環噴泉的「日式」金魚池塘。晚餐後他會從我們的起居室先離開——我們的郊區住宅是那種開放式客廳—飯廳的空間設計,擁有最低限度的隱私,往下幾步階梯就來到他位於地下室的百得工作室。
我在正上方的房間做功課,感受從地面隔板下傳來的震動——他的得偉(DeWalt)旋臂鋸機正在切割木材。有時,他會邀請我來協助。我們一同組裝一件當時流行的人體解剖教學模型「看得見的女人」(The Visible Woman)。她一絲不掛的塑膠軀幹附帶可拆卸的四肢,一具構造完整的骨架外,還有「所有重要的器官」,以及一個塑膠製的展示立架。童年的多數時間,她就在我的臥房裡,站在同樣由父親所建造的一個金屬底座、檯面是厚木板的梳妝檯上;他還把有玫瑰花苞圖案的皺褶布料,用釘槍釘在上頭。
在屬於父親的地下室領域裡,他為自己的家設計出夢想的舞台布景:一台他為母親所建造的桌面可伸縮的縫紉機桌(但母親不喜歡縫紉)。還有一套佔據房間的絕大空間,依真實比例製作的火車玩具組合(以半木結構的小屋、商店、教堂、旅館,還有攜帶著雜貨食品,與把衣物懸掛於細纖維曬衣繩上的村民等,所精心裝飾的北歐風景),還有全配備的汽車加油站(手繪的「飛馬汽車」標誌、汽車修理的起重器、電動車庫門、迷你可樂販售機)。他的兩個孩子小心翼翼地玩著這套玩具,因為摔壞當中任何一個零件,都將成為父親滔滔不絕訓話的理由。之後父親有一項更奢侈的作品——牽線人偶劇場:三聯式的構造物上以滑車與拉繩控制起降的紅色布幕,兩塊用來宣布最新製作的看板,還有讓操偶師置放背板並暗中拉線,位於後台的升橋。以下是我的部分:父親與我以一塊大面積的畫布當作背幕,在其上繪製故事書的內容。他選擇的場景包括:一處黑暗的森林;一處空地上的小屋,周圍是搖搖欲墜的石牆;光影朦朧的臥房內部空間。他選擇的角色包括(施瓦茲玩具店〔FAO Schwarz〕的木製佩爾漢〔Pelham〕拉線人偶):獵人、大野狼、祖母、小紅帽。我演給我弟弟看,也以每張票收取一分錢的費用演給鄰居的小朋友看。至於我父親是否曾來觀賞過演出,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拜訪家人? 」我鄰座的乘客問道。當時我們正在橫跨阿爾卑斯山的飛機上。對方是一位來自中西部,氣色紅潤的退休人員,他和妻子正搭機前往多瑙河乘坐遊輪。我的回應無可避免地讓對話有了後續。
正當我仔細思索該如何回答時,我查看到頭上方的顯示螢幕中,匈牙利航空空中娛樂系統正播放著從法蘭克福到布達佩斯第二段航程的簡短動畫短片,影片裡兔寶寶穿著比基尼與高跟鞋滑過螢幕,艾默小獵人困惑地目瞪口呆。
「一位親戚,」我說。腦中思考著,一個還無法確定的代名詞。
作者資料
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
一九五九年生於紐約皇后區。一九八一年時自哈佛大學畢業,畢業後成為新聞記者。曾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聖荷西信使報》、《亞特蘭大日報》和《邁阿密前鋒報》等報紙寫過文章。一九九一年出版《反挫 》(Backlash)一書,獲得美國國家書評獎(非小說類)(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同年於《華爾街日報》報導喜互惠公司的槓桿收購行為,而獲普立茲釋義新聞獎(Pulitzer Prize for Explanatory Reporting)。 作品有:《恐怖之夢:在不安的美國的神話與厭女主義》(The Terror Dream: Myth and Misogyny in an Insecure America)、《僵局:遭背叛的美國男人》(Stiffed: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Man)、《反挫:誰與女人為敵》(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