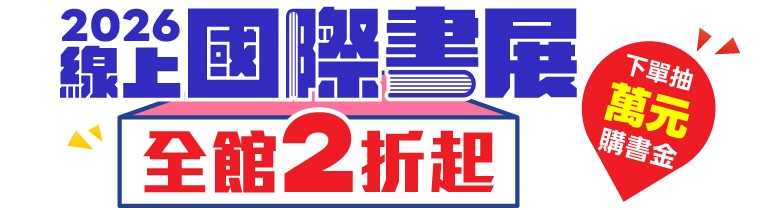- 庫存 = 4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時光庇護所
- 作者:吉奧基.戈斯波丁諾夫(Georgi Gospodinov)
- 出版社:寂寞
- 出版日期:2025-08-01
- 定價:460元
- 優惠價:83折 382元
- ※本商品已最低價,恕不再打折
本書適用活動
分類排行
-
如果他們再次相遇(日記本書衣作家簽名燙金版)(四大網路小說天王破天荒合體!)
-
如果他們再次相遇(翅膀書衣作家簽名燙金版)(四大網路小說天王破天荒合體!)
-
意外的病人(長踞Amazon Kindle「醫療驚悚類」暢銷排行榜!超過3萬多個全球評分的懸疑小說!一個零錯誤率的外科醫師,一場橫跨政、法、醫三界的糾葛!)
-
妖怪日記【首刷限量典藏版】(京極夏彥 × 石黑亞矢子,妖怪大師攜手打造夢幻繪本)
-
懸案對策室
-
如果他們再次相遇(四大網路小說天王破天荒合體!)
-
日花閃爍:台語的美麗詞彙&一百首詩
-
惡意【獨步20週年紀念版】
-
最後的鑑定人(宮部美幸盛讚!破解人性的鑑識天才初登場)
-
奇譚蒐集錄:北方大地的聆神者【日本奇幻文學大獎決選作系列.台灣獨家作家印簽扉頁+跨國訪談】
內容簡介
歡迎來到往日診所,我們幫助您回到最好的時光──
★2023年 國際布克獎得主
★2021年 歐洲斯特雷加文學獎最佳小說
★《衛報》、《金融時報》、《紐約客》年度最佳小說
敬邀光臨往日診所!我們提供受保護的過往時光。
請問您希望置身哪個年代?
解放的六〇?前衛的九〇?或者只要不是現在?
最精緻的文學……我時不時重讀的書。──奧爾嘉.朵卡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一場穿越時間與記憶的奇幻之旅,一部文筆優美且創意豐富的沉思之作,探問過去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們是否能重新找回它,以及它如何定義我們的現在。這是為這個幽閉、無時間感的時代所準備的完美小說。──亞貝托.曼古埃爾,《閱讀的歷史》作者、藏書家
當記憶消失的時候,請速前往時光庇護所,舊日美好我們一一保存,你依然是你,歲月依然靜好。
傳道書: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專治失智症的醫師高斯汀,開設了「往日診所」。
神祕建築物前綴著一朵朵「勿忘我」,而此處採用的獨門療法正是「復刻往日」──由助手採集懷舊碎片:六〇年代的家具、四〇年代的襯衫釦子,某年代的氣味、光線、樂音、聲響……無以名狀的必要細節,分層分室精準呈現,宛如一座座時光隧道,幫助患者解鎖塵封記憶,再次活在那段快樂年歲。
往日療法成效驚人,求診者日增,就連健康人士也期待入住,只為重溫美好舊事。連鎖據點一個個開,規模不斷擴張,從「往日村」到「往日城市」,甚至越洋跨海開設分支。
往日浪潮,洶湧蔓延,引發熱議,有人呼籲國家介入設限,也有支持者提出乾脆公投選定年代,讓整個國家回歸最好的時光!
但,要怎麼把一國、一地逆轉回到某個年代?還有,要挑哪個年代才好呢?
公投熱度升溫,眼看結果就要出爐,一覺醒來的世界會是哪個時空?!甜蜜時光真能得到庇護?或者,「此刻非吾鄉」引爆的是一場終將渾沌的……
內文試閱
◎ 無歸屬者症候群
沒有時間屬於你,沒有地方是你自己的。
你所尋找的,並沒在找你;你所夢想的,並不夢想你。
你知道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代,有屬於你的東西,所以你才會縱橫交錯穿過不同的房間與日子。
但如果你身在正確的地方,那時間卻不對。
而你找到正確的時間,地方又不對了。 不治之症。 ──高斯汀,《迫在眉睫的新療法》
※※※
高斯汀和我創設了我們的第一家往日診所。 事實上,是由他創立,我只是助手,是個往日的採集者。這並不容易。你不能就只是告訴每一個人:好,這是你一九六五年的往日。你必須知道那個時代的故事,如果你沒辦法重新取得那些故事,就必須自己編造。你必須知道那一年所有的事。流行的髮型是什麼樣子?鞋子的鞋頭有多尖?香皂聞起來是什麼味道?要一整套氣味型錄。那年的春天是不是多雨?八月的高溫是幾度?排行榜冠軍的暢銷歌曲是哪一首?那年最重要的故事?不只是新聞,還有謠言八卦,都會傳說等等。情況有時會更加複雜,端視你想召回你面前的是什麼樣的往日而定。
※※※
蘇黎士診所發展得相當好,甚至超過我們的預期。高斯汀占用了整棟公寓建築的頂樓,我們可以創造六○年代的各種變化形態。不久之後,我們獲得擁有整棟樓房的老年精神醫學診所邀請,進一步把我們的理論應用在他們的病房,所以我們實際上可以自由運用整棟建築,於是便開始設置往日房間,同時也在幾個其他國家,包括保加利亞,開設小型診所。
阿茲海默症,或更為一般的記憶喪失,成為世界上蔓延最迅速的疾病。據統計,每三秒鐘,世界上就多出一個失智症患者。登記的個案超過五千萬人──往後三十年間,數量會達到三倍。由於壽命的拉長,這是無可避免的發展。每一個人都會變老。老先生會帶著妻子前來,或反過來,慎重戴上鑽石的老太太帶她們的伴侶前來,被帶來的人尷尬微笑,問他們現在是在哪個城市。有時候是兒子或女兒帶父母親來,他們通常都拉著手,不再認得自己兒女的面容。他們會來幾個鐘頭,或一整個下午,待在他們年輕時代的房間。他們進到裡面,彷彿回到家一般。茶具應該放這裡,我通常都是擺這裡的……他們坐在扶手椅裡,翻看黑白相片的相簿,突然在某幾張照片上「認出」自己。有時候陪他們來的人會帶來他們自己的舊相簿,我們會事先擺在茶几上。也有人會步履蹣跚走幾步,然後回到客廳中央,站在燈具正下方。
有個被帶來的老人家常喜歡躲在窗簾後面。他會站在那裡,像個想玩躲迷藏的老男孩。但這遊戲拉長得沒完沒了,其他孩子早就宣布投降,他們已經回家,他們已經變老,卻沒有人來找他。然而他站在窗簾後面,偷偷往外看,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拖這麼久。躲迷藏最恐怖的事情是,發現再也沒有人在找你。我不認為他會醒悟過來,感謝上帝。
事實上,我們的身體天生就相當仁慈,到最後不是感覺麻木,而是失去記憶。我們的記憶離開我們,讓我們可以玩得更久一點,在童年的淨土樂園再玩最後一次。幾次苦苦哀求,再五分鐘就好,跟從前一樣,到街上玩。在我們被永遠叫回家之前。
※※※
◎ 終點的手冊
我們以前從未想過記憶喪失是會致命的。至少我從未有此懷疑。我一直只把這當成是一種隱喻。一個人突然意識到自己身上承載了多少記憶,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各種層次的記憶。細胞再生的方式也是一種記憶。一種屬於身體、細胞、纖維的記憶。
記憶開始撤離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一開始,你會忘記個別的字彙,接著是臉孔,然後是房間。你在自己家裡找浴室。你忘了你在這一生裡所學到的東西。但你反正學到的也不多,所以很快就會忘光。接著,在黑暗階段──這是高斯汀取的名字──你會忘記在之前累積起來的東西,也就是身體基於本能,在你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所知道的一切。這時,就變得致命了。
最後,腦袋會忘記如何說話,嘴巴會忘記如何咀嚼,喉嚨會忘記如何吞咽。
腿也忘記如何走路。這東西要怎麼再讓它動起來?該死……有人替我們記得如何抬起一腳,如何彎曲膝蓋,劃個半圓,然後在另一腳前面落地,接著再抬起此時已落在後面的這一隻腳,同樣劃個半圓,踩在另一腳前面。先是腳跟,接著是腳掌,最後是腳趾。你再次抬起此刻落在後面的那條腿,彎曲膝蓋……
有人切斷了你身體各個房間的電力。
這病的最後階段其實並不在我們診所的治療範圍,雖然確實也有人在這裡過世。大部分人會到醫院的臨終病房,靠維生系統多撐一段時日,儘管跡象顯示,身體已經拒絕供應生命所需。身體逐步殺死自己,一個器官接著一個器官,一個細胞接著一個細胞。身體也受夠了,它們累了,想要休息。
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方能聽見身體的這個渴望。瑞士除了是現世之人的天堂之外,也是垂亡之人的天堂。一連數年,蘇黎士不可免地成為全球最適人居的城市。這裡也可能是排名第一,最宜死去的城市,但令人驚訝的是,並沒有這樣的排名,至少正式來說沒有。最宜死去的城市。當然,這是針對那些負擔得起的人。死去已經變得相當昂貴。但死亡有什麼時候是不要錢的嗎?用藥丸也許稍微貴一點,用槍則比較困難,至少在你雙手握到槍之前並不容易。但有其他比較簡單,而且完全免費的方法──溺水、從高處跳下、上吊。我認識的一個女人告訴我:「我想過要從屋頂跳下,但一想到摔落地上之後,我的頭髮會有多亂,而且天曉得我的裙子會有多皺,還沾上污漬什麼的,我就覺得太丟臉了,於是放棄這念頭。畢竟,碰到這樣的狀況,他們會拍照,沒錯,別人會看到……」
喏,這就是身體健康的徵兆──會覺得丟臉,會預見尚未發生的事,會想到未來,甚至想到自己死後,還會虛榮。真正渴望死亡的身體不再有這樣的虛榮心。
簡而言之,如果你想了結自己,有各式各樣免費的方法。但是當你不再有氣力動手呢?甚至不只是沒氣力,連如何動手也不記得了,會怎麼樣呢?你要怎麼離開這個人生?該死,他們把出口藏到哪去了?你永遠無法第一手取得這個經驗,說不定你試過一兩次,但是都不成功。(事實上,自殺未遂才是真正的悲劇,而那些成功的,就只是走完程序了。)到底要怎麼做?求神悲憫哪,人才能殺死自己,退化的大腦很想知道,書裡教人怎麼做來著?應該是和喉嚨有關,喉嚨出了問題,空氣,你不再吸進空氣,或是有水灌進來,把你像個瓶子那樣灌滿……再不然就是深深割幾道,還有繩子,但是我要拿繩子做什麼……?
於是有了幫助自殺。這個表達方式真特別。情況慘到如果沒有人幫助,你就什麼也做不了,甚至連想死都做不到。
在如此絕望的處境裡,有種服務出現了。要是你的狀況是可以自己訂購這項服務,自己付費,那你很幸運。如果不行,那你就是給你最親近、最心愛的人製造了很多麻煩與花費。問題是,他們付錢讓人殺了你,要如何不覺得自己是殺人凶手。確實,人類文明已經相當進化,如今你必須為謀殺取得正當性。千萬別低估文明在這方面的作用。我們總是會為這樣的事情想出美麗的名字。優—蓮—埃—夏亞(Eu-than-a-sia) ,聽起來像是希臘女神的名字。這是善美之女神,美好的死亡。我想像她手裡拿的不是權杖,而是細長的針筒。「安樂死是為了受死之人的利益而執行的死亡。」這文字聽起來好拗口,但是必須為這個舉動取得正當性,所以痙攣,扭曲,最後變成無止盡的迴圈。我殺你,是為了你好,你會明白(怎麼可能不明白)這樣對你比較好,這樣痛苦會消失。
我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一行在這個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安樂死很適合這裡。起初是非法的,接著是半合法。每個人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像許多其他時代一樣,讓私人診所有機會歡迎來自歐洲各地想要尋求死亡的人。更準確來說,是來自歐洲的某一部分。至於另一部分的歐洲,我們這個部分的人,是得不到這個機會的。我們甚至沒有安樂死,也從來都不關心安樂死。在共黨統治下的死亡,可不是睡在真絲床單上那般奢侈的事。更何況,沒有人會發給你護照簽證,讓你在不保證一定回來的情況下,帶著單程機票出國。你去了,死了,就自動成為叛國者。你會因此被判死刑。在你死後,在缺席審判的情況下被判死刑。
瑞士是安樂死國度。如果你想找一個可以住下來等死的好地方,這兒可以幫你。有趣的是,這個死亡產業並未正式納入旅遊指南、觀光手冊。旅遊指南之所以創造出來,前提是建立在某個人活著,並且正在旅行的幻想。這是基本的設定。死亡並未收入在這世界上的任何一份旅遊指南裡。多大的遺漏啊!
但當某人的啟程時間已經接近的時候呢?當他已經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旅人呢?為什麼我們還在等待寫給這些旅人的旅遊指南呢?說不定這種指南早就存在了,誰知道呢?
死亡之旅(Sterbetourismus),我幾乎可以確定這個詞最早是在瑞士被想出來的。數據顯示,每年有大約一千名外國人,主要是德國人,也有不少英國人,而且不只是絕症末期的人。年老夫婦因為其中一人已到絕症末期,決定提前一起離開。我可以想像他們抵達此地的情況,態度溫和,微微有些不安,手拉著手。就像這樣,他們手拉著手,經歷所有的程序。他們不希望在那無邊無際的極樂天堂某處失去彼此,因為他們不可能約定時間和地點來會合。
費用。費用是多少,究竟?我在這個領域深入挖掘。事前的準備工作大約要七千瑞士法郎。葬禮和全套儀式,要一萬瑞士法郎。若是你僱個殺手來動手,那肯定更貴,也更不舒服。
說不定情侶檔會有折扣。但還是要說,對於這樣的國家來說,七千法郎不算什麼大數目。所以,他們應該是靠來客量夠多賺錢的。你想想其他東西都還要更貴……在萬物漲的時候,人命的價格顯然下滑。儘管有史以來,人類的死亡一向就很廉價,但來到二十世紀,價格更是低到氣死人。沒錯,他們的營業額確實很高。
另一方面,真正的成本又有多少?十五毫克的戊巴比妥2 粉末?在墨西哥,你可以找任何一位獸醫,說你想讓家裡的老狗安樂死,他們就會開這個藥給你。
我仔細研讀其中一個單位,應該是個非營利組織的網站。網站相當簡陋,是綠色的。我從沒把死亡跟綠色聯想在一起過。最上方的標語是,活得有尊嚴,死得有尊嚴。這看起來更像是日本武士的訓示,要真是那樣還比較說得通。一張簡單的照片,是整個團隊的合照,看得讓人心裡不由得毛了起來──他們全都咧開嘴露出大大的微笑,還張開手臂。這團隊有多大?十二個人,就像耶穌的十二門徒。是刻意的嗎?我懷疑。二○○五年,其中一個變成猶大,洩露內部消息,說這個組織是「收費高昂的死亡機器」。
網站上沒有評論,也沒有保證退款的服務。
過程絕對無痛、無風險,他們給我的醫療宣傳小冊上這麼說。但這不是會威脅生命嗎?該死,難道他們真正想說的是,你不會有腸胃不適、便秘、血壓急降或成癮的危險?
夏季的某幾個月也有折扣。大家偏愛的死亡時間顯然主要是冬季。我很好奇,這種折扣會吸引更多人前來嗎?都要為自己唱輓歌了,沒有道理還當小氣鬼吧,你大可以讓自己享受相當程度的奢華。我假設死亡的掮客與祕密經理人(他們勢必存在,以旅行經紀當偽裝)會好好善加利用這個機會。加長型黑色禮車,空間足以放進擔架,你若是臥床,要能載你沿著歐洲的高速公路奔馳。如果病人渴望,同時條件也允許的話,可以在奧地利停留一晚,在蘇黎士湖畔度過下午。回程,禮車當場變靈車,載骨灰罈直接回去,中途不必再到任何地方停留。
死亡之旅是提供給有錢人用的,窮人用不著安樂死。
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量殺戮與集中營的死亡產業之後,歐洲人比較難容許提供優質好死的產業存在。這導致當年出於必要而採取的中立政策的瑞士,成為值得小心呵護的獨占者。正如高斯汀所言,今天你在歐洲抓住的任何事物,都會把你領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年之後,一切都不再相同了。
我去看他們進行儀式或程序的那棟建築,完全平凡無奇。看起來更像間外面有塑膠壁板的兩層樓大棚屋。從網站上的照片來看,裡面的裝潢也同樣簡樸。一張床,一個床頭櫃,牆上一幅畫,兩把椅子。有幾個房間的窗戶可以眺望湖景。
我試圖以冷漠且嚴格的態度閱讀所有東西,這樣我就不會去思索最主要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在整個過程裡,我想像的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父親。科技非常淺顯明白,但是問題仍在,你如何面對罪惡感?我父親似乎察覺到了,以微妙的方式助我一臂之力。就像父母親一輩子都悄悄為孩子犧牲自己那樣,他自己過世了。在他彌留期間,我陪在他身邊,握著他的手。我很想知道,如果可以的話,他會希望用他僅餘的記憶細胞去感覺什麼。我從我們七○年代儲藏室的東歐備品裡,拿出空姐牌香菸,點起一根。我父親是我所見過最優雅的抽菸者。我偷偷點燃人生第一根菸時,就是想模仿他。現在我代替他抽一口菸,發現他的鼻孔微微抽動,眼皮也感覺到變化。接著,他就平靜下來了。
最後一個記得我童稚模樣的人離開了,我對自己說。就在這時,我才哭了起來,像個孩子似的。
延伸內容
譯後記
莫忘,心中的那道光\李靜宜
身為國際關係研究者,不時覺得沮喪挫敗,特別是在世界以瘋狂速度朝四面八方漫無目標狂奔的此時。
求學期間,有位剛從美國頂尖大學拿到博士學位返國任教的年輕老師,對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我們再三叮囑:「以後寫博士論文,一定要趁早寫完!」因為他隨口都可以舉出這個那個例子,說某位出色的同門同學,研究最熱門的冷戰議題,論文拖拖拉拉沒寫完,然後一覺醒來發現冷戰突然結束了,多年研究付諸流水,博士學位成為夢幻泡影……
那是一九九○年代,即將跨進新世紀之前的最後幾年,世界起了地覆天翻的變化:宰制地球幾乎每一個面向的冷戰一夕結束,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東歐集團瓦解,民族國家紛紛獨立,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吶喊著西方民主制度的勝利,代表了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
於是,在邁向新世紀之際,整個世界洋溢著近乎天真的樂觀昂揚,和平已取代衝突,合作將替代對抗,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與歐盟的整合,在在預示了人類歷史無可抵擋的必然發展。
然而,誰也沒想到,輪到我們自己寫博士論文時,研究當時最熱門的區域整合議題,卻拖拖拉拉沒把論文寫完的同學,等來的不是全球經濟整合帶動的政治整合,而是歐盟的實際運作證明跨國整合只是個過度美化的夢幻,於是,我們也有了這位那位出色同學永遠拿不到博士學位的悲哀故事可以講述。
只是,二十世紀末期學術研究的挫敗,迎來的是舊時代惡夢的結束,而二十一世紀面對的,卻是新時代美夢的破碎。歷史並未終結。
想想,國際關係研究者就像在海濱蓋沙堡的人,仔細研究沙石質地,縝密規畫構造格局,認真搭蓋起宏偉城堡。然而,我們自以為透過邏輯理性分析所得的嚴謹理論模型,禁不起一天的潮起潮落。浪濤拍來,退去,矗立的堡壘消失於無形,彷彿不曾存在過。
歷史並未終結,只是朝著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向奔馳。我們為未來所設想的一切,全都沒發生,而我們以為不會再重蹈覆轍的一切,卻一次又一次在世界各個角落重新萌生。至此,我們幡然醒悟,這個世界經歷一整個世紀的殘酷戰亂與仇恨對峙之後,唯一獲得證實的真實教訓就是,人類永遠不曾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總是在這樣的時刻,深深感受到小說家遠比研究者更勇敢,也更有創見。面對無法想像的未來,我們何不從此時此刻往後倒退幾步,回到往日,那麼,我們面對的未來,就會是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日子,儘管是「二手」的未來,但終究是未來,總比一無所知的未來好,吉奧基.戈斯波丁諾夫在《時光庇護所》裡提出了這個有趣的想法。
小說的開始,是在「時間零度」的瑞士專為阿茲海默症患者創設「往日診所」,以還原某個特定年代的房間,讓喪失記憶的人找回他們最舒適自在的時光,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
但是,需要回到往日找尋安慰的,何止是喪失記憶的人,正常人也需要一座庇護所,以熟悉的往日抵禦陌生的時光襲擊。於是,對往日的狂熱開始淹沒世界,越來越多人渴望擁有集體記憶,擁有可以投注共同情感的往日,儘管這樣的集體記憶,有時必須扭曲自己的個人記憶,以符合當下的集體需求。
以一個房間為病患創造往日的診所,有沒有可能擴展成一整座城市,一整個國家,甚至一整個跨越國界的區域呢?一個個隔絕於線性時間之外的往日世界,或投射了我們對往日榮光的嚮往,或反映了我們對現實處境的絕望,小說家以這看似荒謬的故事設定,道出了我們內心最深沉的恐懼:愛的時代已經結束,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恨的時代。歷史再次倒退,世界再度在硝煙瀰漫中沉淪。
自我毀滅,難道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宿命?
初春,偶然得了一把久聞其名,卻是第一次真正眼見的勿忘我。纖巧嬌俏的靛藍花朵生命力堅強,綿綿不絕綻放,宛如神話中在森林裡急著對花神呼喊:「不要忘了我!」的迭聲輕喚。
《時光庇護所》裡,位在蘇黎士湖畔的往日診所大門外,也有星星點點的藍色勿忘我,在鮮翠欲滴的「瑞士綠」草地上連綴成最美的春景。治療阿茲海默症的診所門口開滿勿忘我,是某種諷刺嗎?我想不是的。在春風裡款款輕擺的勿忘我不是諷刺,而是期待。
未來也許是一匹狂飆的野馬,但唯一能給牠套上韁繩,導歸正軌的,只能是人性中或許稀微,卻始終不曾泯滅的某種光,會共情,會悲憫,會為失去的一切哀悼,為可能的未來懷抱渴望的那道光。
正如生命力強韌的勿忘我,會在地底沉睡數十年,靜靜等待時機成熟,才緩緩甦醒,在第一道春風吹過時,萌出新芽,從綠草地裡開出靛藍花朵,提醒我們:「莫忘!」
莫忘,歷史的解答不在於時間的前進倒轉,而在於我們心中的那道光。
莫忘。
◆這部小說令人深思,也值得我們警惕;它同時深具感動力,因為那敏感又精準的語言,以一種普魯斯特式的筆觸,捕捉了過去極度脆弱的本質。
──國際布克獎獲獎評論
◆最精緻的文學……我把這書放在書架上一個特別的格子,專門收藏那些值得時不時重讀的書。
──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犁過亡者的骸骨》作者
◆兼具玩味與深刻,《時光庇護所》讓哲學變得迷人,讓日常變得非凡。我非常喜愛這本書。
──克萊爾.梅蘇(Claire Messud),《樓上的女人》作者
◆戈斯波丁諾夫是歐洲最迷人且無可取代的小說家之一,而這是他最宏大、最有靈魂、最能撼動人心的一本書。
──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圓圈》作者
◆《時光庇護所》是一場穿越時間與記憶的奇幻之旅,一部文筆優美且創意豐富的沉思之作,探問過去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們是否能重新找回它,以及它如何定義我們的現在。這是為這個幽閉、無時間感的時代所準備的完美小說。
──亞貝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閱讀的歷史》作者、藏書家
◆在這部荒誕的歐洲政治幻想小說中,作者戈斯波丁諾夫以虛構的自己為敘述者,講述一位神祕友人創建了一間「往日診所」──透過重建患者尚能記得的舊日環境,來安撫阿茲海默症者的心靈。作者以「歷史仍是新聞」來巧妙地指出過去如何滲透、甚至侵蝕損害當下的現實。
──《紐約客》,二○二二年度最佳書籍
◆這本小說的核心議題是,以人為手法返回過去的道德爭議,以及這是否真能予人安慰──沉溺舊時究竟是治癒,還是傷害……作者對那些來自過去的事物懷有同情與感傷之情──過時的物品、老牌咖啡、老唱片跳針的聲音──但他拒絕將全球化、移民與現代化當成這些事物消失的代罪羔羊;我們每個人都參與了歷史的毀滅,而倒退只會帶來偏狹與對傳統懷舊庸俗的吹捧。讀到這裡,很難不聯想到脫歐、「美國再次偉大」或普丁的大俄羅斯復興主義背後的反動情緒,但作者筆法相當細膩,不致淪為粗糙的政治諷刺……感人又睿智。
──《紐約時報》書評
◆這是一部關於時間本身的編年史──這正是保加利亞當代最傑出作家戈斯波丁諾夫在《時間庇護所》中所展現的雄心壯志。這部作品於新冠疫情席捲歐洲前夕在柏林完成,讀來不時讓人感到一種不安的先知感,彷彿對身體、政治乃至形而上層面的「感染」提出警告。 戈斯波丁諾夫骨子裡是一位詩人。他能用一句話寫出一整本小說:「往日是我的祖國……」他以保加利亞特有的傷痛與鄉間的荒涼貧窮為背景,揭開深沉的歷史傷口。
──《Astra文學雜誌》
◆這部融合奇幻與現實的小說,以一種新穎療法為核心,探索懷舊的力量是否真能療癒人心,是戈斯波丁諾夫繼《悲傷物理學》後又一力作。小說筆法靈巧,將看似荒誕的設定注入濃厚的感傷與渴望……是一部耐人尋味、充滿尖銳諷刺的作品,堪與卡夫卡並肩。
──《出版人週刊》
◆這本極富哲思的小說,與其說是寫實文學,不如說是一則寓言,警示人們回看過去的危險。小說後半部節奏明快,充滿一種令人著迷的波赫士式奇異感,同時也提出警告:記憶不但會失誤,甚至可能帶來危險。這是一部充滿野心、古怪奇異、玩味時空的小說。
──《柯克斯書評》
◆戈斯波丁諾夫是保加利亞最受歡迎的當代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懷舊藝術家。他的作品和奧罕.帕慕克、安德烈.馬金尼類似,都執迷於記憶,那既模糊曖昧又令人感傷的吸引力……這部非常值得一讀的小說,以歐洲再次來到衝突邊緣的畫面作結—此一想像場景如今因現實事件而變得駭人又真實。
──《華爾街日報》
◆這是一部極具突破性的思想類型小說。本書談論記憶──它如何褪去,又如何在迷茫個體的想像以及國家的公共話語中被恢復,甚至重新創造。
──《泰晤士報》
◆再合時宜不過了……既幽默又荒誕,但同時令人不寒而慄,因為當戈斯波丁諾夫把這個想法當作虛構玩笑時,讀者開始感受到某種更貼近現實的東西……他是位溫暖又技藝高超的作家。
──《衛報》
◆小說提出許多引人入勝的問題:如果社會變得如此害怕未來,以致我們注定要不斷重溫熟悉的過去,明知其中藏有恐怖與歧途,我們會怎麼辦?而如果我們已經走在那條路上呢?
──《洛杉磯書評》
作者資料
吉奧基.戈斯波丁諾夫(Georgi Gospodinov) 歐洲最迷人且無可取代的小說家之一 1968 年生於保加利亞揚博爾,是該國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創作涵蓋詩歌、散文、小說、圖像小說、歌劇劇本、短片劇本等多種體裁。1999年,處女作《自然小說》出版,之後翻譯成二十多國語言,是當代譯介最廣的保加利亞作品。 他的文字充滿尖銳諷刺和抑鬱幽默,與米蘭.昆德拉等作家的風格一脈相承,並被譽為「來自東方的普魯斯特」。他常從保加利亞的社會、政治,以及外界對東歐的看法中獲得靈感。 第二本小說《悲傷物理學》獲得國際高度關注,有評論將他與馬奎斯、帕慕克並列,該書也被喻為「保加利亞的百年孤寂」,迄今仍在保加利亞暢銷小說之列。 2017年,他的短篇小說〈盲眼維莎〉改編成短片,並入圍奧斯卡最佳短片。 最新作品《時光庇護所》在拿下義大利斯特雷加文學獎歐洲獎後,又於2023年榮獲國際布克獎,並成為《衛報》、《金融時報》、《紐約客》年度最佳小說。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