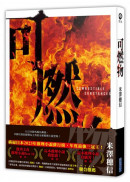- 庫存 = 4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內容簡介
目錄
內文試閱
作者資料
張亦絢 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暨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著有《愛的不久時》、《永別書》(以上國際書展大獎入圍)、《性意思史》(Openbook與鏡文學年度好書獎)、《我討厭過的大人們》、《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感情百物》等數種。專欄「我討厭過的大人們」獲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麻煩電影一下」(BIOS Monthly)、「想不到的台灣電影」(《FA電影欣賞》)作者。曾任台北藝術大學、臺灣大學川流臺灣文學講座駐校作家。曾於德國柏林駐村、二〇二四年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作家。《永別書》獲《文訊》頒發「二十一世紀上昇星座」榮譽,並為二〇一七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臺灣館選書。她也為臺灣文學館策展。 網站:nathaliechang.wixsite.com/nathaliechang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康乃爾大學名譽教授,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著有《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美國殖民時期之暹羅政治與文學》(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的想像》(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等書,以及回憶錄《椰殼碗外的人生》(時報文化)。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