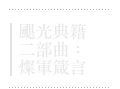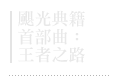|
[六年前]
加絲娜.科林假裝很享受宴會,完全沒有洩露她打算派人殺害其中一名客人的跡象。
她穿梭在擁擠的饕宴大廳,仔細聆聽動靜。酒液潤滑了舌頭,愚蠢了腦袋,她的叔叔達利納玩得很盡興,正從上桌前站起,叫喊帕山迪人讓鼓手出來,加絲娜的弟弟艾洛卡衝上前要他叔叔別再說了──雅烈席卡眾夫人們都很有禮貌地假裝沒聽到達利納的喊叫,艾洛卡的妻子愛蘇丹則用手帕捂著嘴偷笑。
加絲娜轉身背向上桌,繼續穿梭在房間之中。她跟殺手有約,因此迫不及待想要離開悶熱的室內,這裡混合了太多不同香水的空氣已經發臭;火光活躍的壁爐對面,四人女子橫笛樂團在高台上演奏音符,但早就讓人聽得發膩。
加絲娜跟達利納不一樣,她總是能吸引人們的目光,如同蒼蠅被腐肉吸引那般,那些眼睛總是追隨著她,像是嗡嗡搧動的翅膀低語。如果說雅烈席卡宮廷裡有比酒釀更受歡迎的東西,那一定就是流言。所有人都知道達利納會在宴席上喝得形象盡失──但是國王的女兒承認自己信奉異教?這是前所未有的事。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加絲娜才這般直言不諱。
她經過帕山迪使節團。他們聚集在上桌周圍,以饒富韻律感的語言交談著。雖然這個慶祝會的主題是身為上賓的帕山迪人以及他們剛剛跟加絲娜的父親簽署的協定,但他們看起來並不投入,甚至一點都不開心。他們看起來很緊張。當然啦,他們不是人類,所以有時候的反應令人摸不清。
加絲娜想跟他們聊聊,但是她約好的會面不等人。她刻意把約會定在宴會進行一半的時間點,好趁所有人都注意力分散、醉醺醺時離開。加絲娜走向大門,卻突然停住腳步。
她的影子,方向居然是反的。
悶熱、吵鬧、熙攘的房間突然顯得很遙遠。薩迪雅司光爵穿過加絲娜的影子,但影子很明顯指向附近牆上的錢球燈。薩迪雅司專心與人交談,並沒有注意這個異狀。加絲娜盯著影子,冷汗直冒,胃部緊縮,感覺很想吐。不要又來了。她尋找另一個光源,一個原因。找得到原因嗎?找不到的。
影子徐徐地溶向她的方向,凝聚在她的腳邊,然後朝正常方向延展。她渾身一鬆。有沒有別人注意到?
幸好,在她以目光環掃一圈後,並沒有發現任何驚恐的注視。人們的注意力全被帕山迪鼓手吸引了,如今他們正在一片敲擊聲中穿過門廊,準備架設樂器。加絲娜皺眉,注意到一名不是帕山迪人的僕人,身著鬆軟的白衣在協助他們。雪諾瓦人?很罕見。
加絲娜定下心神。她這樣發作是什麼意思?鄉野傳說迷信裡,作怪的影子代表人被詛咒了。她向來將這種事斥為無稽之談,但有些迷信來自於事實,她的另類經驗早已證明這點。她需要進一步調查。
平靜、探究的思緒跟她冰冷的皮膚與順著脖子留下的冷汗相比,感覺像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可是隨時保持理性很重要,不只在一切平靜無波的時候。她強迫自己出門,離開悶熱的房間,進入安靜的走廊。她選了通常只有僕人走的後門,這是最直接的道路。
在這裡,穿著黑白妝束的上僕正在服侍光爵光淑們。她早就料到這番光景,但沒料到的是她父親就在前面,正和梅利達司.阿瑪朗低聲交談。國王在這裡幹什麼?
加維拉.科林國王比阿瑪朗矮一些,但是阿瑪朗在國王面前保持微微躬身的姿勢,這在加維拉身邊是很常見的情形。國王說話的語氣往往輕柔卻充滿魄力,讓人忍不住俯身傾聽,捕捉字字句句與其中的含義。他是個英俊的男人,跟他的弟弟不同的鬍形勾勒出而非掩飾住堅毅的下巴,加絲娜覺得至今沒有傳記作者能傳達他的個人魅力與魄力。國王親衛隊隊長提瑞姆立在他們身後,穿戴著國王的碎甲。國王最近已經不再穿碎甲,偏好將碎甲交給提瑞姆,這位隊長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劍術大師之一。加維拉自己則改穿古典款式的尊貴王袍。
加絲娜回頭瞥了饕宴大廳一眼。她父親是什麼時候溜出來的?她責怪自己的粗心。妳出來前應該先看看他是否還在裡面。他在前方不遠處一手按著阿瑪朗的肩膀,一手手指懸空,憤怒卻低聲地說著話,加絲娜聽不清楚。
「父王?」她開口。
他瞥向她。「啊,加絲娜,這麼早就要休息了?」
「一點都不早了。」加絲娜優雅地走上前。很顯然加維拉跟阿瑪朗兩人溜出來進行私密談話。「這個時候的宴會已經到了讓人厭煩的階段,高談闊論多了,內容卻沒變得更有意義,談話的對象大多已經醉了。」
「很多人反而覺得這樣很愉快。」
「可惜很多人都是白癡。」
她的父親一笑,「對妳來說,很難熬嗎?」他輕柔地問。「跟我們其他人同生於世,忍受我們平庸的智商與簡單的思想?妳獨一無二的聰明睿智讓妳覺得寂寞嗎,加絲娜?」
話中的責難意味讓加絲娜發現自己滿臉通紅,就連她母親娜凡妮都沒辦法讓她如此羞愧。
「如果妳找得到愉快的誘因,也許就會喜歡宴會了。」加維拉的眼睛瞥向阿瑪朗,他一直覺得這個人跟他女兒很匹配。
但那永遠不可能成真。阿瑪朗與她對視一下,便低聲向國王告退,快步從走廊離去。
「您叫他去辦什麼事了?您今天晚上在安排些什麼?」
「當然是和約啊。」
和約。他為什麼這麼在乎?其他人都建議征服帕山迪人或是不理他們,加維拉卻堅持要跟他們和談。
「我該回慶祝會去了。」加維拉示意提瑞姆,兩人順著走廊走向加絲娜剛才通過的門。
「父親?您有什麼事情沒告訴我?」加絲娜說。
他回頭看著她,目光平穩,淺綠色的眼睛是他良好出身的證據。他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擅長洞悉人心了?颶風的……她覺得自己幾乎不認得他了。這麼短的時間,這麼明顯的改變。
從他端詳她的方式看來,像是他並不信任她。難道他知道她跟利絲見面?
國王一語不發地轉身,返回宴會,衛隊們跟在後面。
這個皇宮是怎麼了?加絲娜心想,深吸一口氣。她得進一步探究。希望父親沒發現她在跟殺手們見面──但如果他知道了,她再隨機應變就行。他一定能理解,總要有人盯著家裡,最近他所有注意力都被帕山迪人吸引去了。加絲娜轉身,繼續往前走,經過一名向她鞠躬的上僕。
在走廊裡走了一段時間之後,加絲娜注意到她的影子又變得怪怪的。她煩躁地嘆口氣,看到它又伸向牆上的三盞颶光燈。幸好她已經離開了人來人往的區域,這裡也沒有僕人。
「好了,夠了。」她叱罵。
她原本沒打算開口,可是隨著她說出口的話,幾個在路口遠處的影子突然動了起來。加絲娜一口氣梗在喉頭。影子變長,變深,出現了人影,越來越長,越來越高,站起來了。
颶父啊,我要瘋了。
其中一道影子變成漆黑的人形,微微帶著一點光澤,像是油做的人。不對……是某種別的液體,但外表泛著油光,讓它看起來既黑又亮。它走向她,抽出劍。冰冷明確的邏輯指引著加絲娜,喊來人太慢,這個怪物漆黑流暢的動作訴說著它的速度一定比較快。
她站在原地,迎向怪物的注視,讓怪物忽然間遲疑了,它後面有一小群其他怪物也在黑暗中現形。好幾個月以來,她一直察覺到它們的目光。
這時,整條走廊已經變黑,彷彿逐漸陷入無光的深淵。加絲娜心跳加快,呼吸急速,舉起手朝旁邊的大理石牆伸去,想要觸碰實實在在的東西,但她的手指卻微微陷入了岩石,彷彿牆壁都變成了泥巴。
颶風的,她得想個辦法。什麼辦法?她能怎麼辦?
在她面前的身影瞥向牆,離加絲娜最近的壁燈變黑,然後……
然後皇宮崩解了。
整棟建築物碎裂成小玻璃球幣,像是千千萬萬顆珠子那樣。加絲娜尖叫,向後仰摔入黑色的天空。她已經不在皇宮裡,她在別的地方──另一片土地,另一片時空,另一片……不知名。
她眼前只剩下黑暗豐潤的身影,懸浮在空中,似乎正滿意地收起劍。
加絲娜撞上什麼……是玻璃珠累積成的海洋。無數的玻璃珠落在她身邊,像是冰雹般落入奇怪的海洋。她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地方,無法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或是有什麼意義。她一面掙扎,一面沉入似乎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是玻璃珠,她看不到玻璃珠以外的地方,只感覺自己不斷地陷入翻騰、窒息、撞擊聲不絕的地方。
她要死了。但她的工作還沒完成,她的家族無人保護!她永遠不會知道答案。
不。
加絲娜在黑暗中掙扎,珠子滾過她的肌膚,卡在她的衣服裡,在她想要游泳時還滾入她的鼻腔。沒有用,她在這片材質中沒有任何浮力。她將手舉在嘴前,想要圍出一塊空間方便呼吸,一時間她成功了,能夠短促地吸氣,但是珠子順著她的手滾動,硬擠入她的指縫。她繼續往下沉,速度變得更慢,像是緩緩沉入黏膩的液體。
每顆碰到她的珠子都讓她有某種隱約的感覺。一扇門。一張桌子。一隻鞋子。
珠子滾入她的口中。這些珠子似乎可以隨意移動,它們會嗆死她、摧毀她。不對……不對,它們似乎被她吸引。她突然有個念頭,不是清晰的想法,而是一種感覺。
它們對她有所求。
她抓住手中的一顆珠子,珠子給了她杯子的感覺。她給了它某種……東西?她周圍的其他珠子聚集在一起,相互連結,像是被水泥封在一起的岩石。一瞬間,她突然落下,不再是一顆顆珠子,而是一堆珠子,黏在一起形成了……
杯子。每顆珠子都是一個圖形,是給其他珠子的指引。她放開手中的珠子,周圍的珠子也跟著散落。她揮動手腳,隨著呼吸用盡,慌亂地拚命尋找。她需要可以使用的東西,有用的東西,能夠活命的辦法!她別無選擇地攤開雙臂,盡量去碰觸珠子。
一個銀盤。一件外套。一座雕像。一盞油燈。
然後,一樣古老的東西。
沉重,思緒緩慢,卻強大。是皇宮。加絲娜慌亂地抓住這顆珠子,把力量灌注進去。她的意識開始模糊,但是她仍然朝這顆珠子灌注她的一切,然後命令它升起。
珠子動了。
一陣澎湃聲中,珠子相互撞擊、敲打、碎裂、晃動,幾乎像是浪花拍打在岩石上的聲音。加絲娜從深處升起,某種堅實的東西抵在她腳下,服從她的命令。珠子敲打著她的頭、肩、手臂,直到她終於衝出玻璃海面,將一捧珠子灑入黑色的天空。
她跪在小珠子相互黏接形成的玻璃平台上,舉起手,抓住似乎是指引的珠子。其他珠子滾到她身邊,形成走廊的形狀,牆壁上有油燈,前面有交叉口。看起來形狀不太對──當然,因為一切是珠子形成的,可是也相當逼真。
她不夠強大到能夠形成整個皇宮。她只創造了走廊,連屋頂也沒有,但地板支撐住她,讓她不會再沉下去。她呻吟地張開口,珠子從嘴巴掉出來,喀啦喀啦地落在地面,然後她一邊咳嗽,一邊吸入甜美的空氣,汗水順著她的臉頰滾下,匯集在她的下巴。
黑色的人影又踏上平台,在她面前再次抽出劍。
加絲娜舉起第二顆珠子,是她之前感應到的雕像。她給了它力量,其他珠子在她面前聚集起來,集合成宴會廳前面的其中一座雕像──戰爭神將,塔勒奈拉.艾林。一名高大、渾身肌肉的男人,手中舉著一把巨大碎刃。
它不是活的,但是她可以讓它動起來,揮下珠子聚成的劍。只是她懷疑它有多少戰鬥力,因為圓珠沒辦法開出銳利的刀鋒,不過這個威脅仍然讓黑色的身影遲疑了。
加絲娜一咬牙站起,珠子從衣服上滾下。不論那是什麼東西,她絕對不會跪在它面前。她站到珠子雕像旁邊,第一次注意到天上奇怪的積雲似乎形成一條長長大道,筆直而綿長地指向天際線。
她與油人對望。它看了她一陣,然後舉起兩隻手指到額頭,彷彿尊敬地鞠躬行禮,一襲披風在它身後揚起,其他油影聚集在它後方,紛紛開始交頭接耳起來。
珠子之界驟然消失,加絲娜發現自己回到皇宮的走廊。真的皇宮,有著真的石頭,只是一切都變暗了。牆上油燈裡的颶光完全耗盡,唯一的照明來自走廊盡頭。
她背靠著牆,深呼吸,心想,我要把這段經歷寫下來。
她寫下來之後會進行分析跟思考。不過現在她只想馬上離開這個地方,她快步而行,不在乎走向哪裡,只想逃離她覺得還在注視自己的眼睛。
沒有成功。
終於,她穩住心神,用手絹擦掉臉上的汗。幽界,她心想,童話故事把那裡稱為幽界,是各種靈的神話王國。她從來沒相信過神話。如果在歷史裡仔細查找,一定可以找出任何事的蛛絲馬跡,幾乎所有發生的事情,之前都發生過。這是歷史的偉大教訓,而且……
颶風的!她約定好的會面。
加絲娜一面咒罵自己,一面急急忙忙趕路。剛才的經驗一直讓她忍不住要回想,但是她必須赴約,所以她繼續下了兩層樓,離帕山迪的鼓聲越來越遠,直到只聽得見幾聲最響亮的敲打。
帕山迪音樂的複雜程度每每都讓她相當意外,暗示他們不是眾人以為的野蠻人,隔著這麼遠的距離聽起來,居然有點像那個黑暗之界的珠子敲擊的聲音,讓人心驚。
她故意挑了這個人跡罕至的皇宮一角跟利絲見面。一名加絲娜不認得的男子靠在約定的門外,讓她鬆了一口氣。這個守衛應該是利絲的新僕人,他在這裡意味著雖然加絲娜遲到,但利絲還沒離開。
她穩下心神,朝鬍子裡夾雜著紅點、粗壯的費德人守衛點點頭,推開門走了進去。
利絲從小房間裡的桌邊站起,她穿著女僕的衣服,胸口開得很低,看起來像是雅烈席人。或是費德人。或是巴伏人──端看她選擇強調哪一部分的血統。利絲的長髮自然披散,圓潤誘人的身材讓她引人注目得恰到好處。
「光主,您遲到了。」利絲說。
加絲娜沒有回應。她是雇主,不需要解釋什麼,所以她只是將東西放在利絲身旁的桌上。
一個小信封,用小惡魔蠟彌封。
加絲娜用兩隻手指按著信封,陷入思索。
不行,這太衝動了。她不知道父親是否知道她在做什麼,但就算他不知道,皇宮裡最近出的狀況也太多,除非更有把握,否則她不能進行刺殺行動。
幸好她有備案。她從袖子裡的內袋取出第二個信封,放在桌上,移開手指,繞過桌子坐下。
利絲坐回原位,信封消失在她的胸前。「光主,選擇在這一夜叛國……有點奇怪。」
「我僱用妳只是為了盯著對方。」
「抱歉,光主,一般人不會僱用殺手只是為了盯著對方。」
「信封裡有指示,還有頭款。我選擇妳是因為妳擅長長期觀察,這是我需要的。現在先暫時這樣。」
利絲微笑,但點了點頭。「監控王位繼承人的妻子?這樣會比較貴。您確定不想要她死?」
加絲娜的手指敲打著桌面,這才發現她正應和著樓上的鼓聲。這個音樂複雜得出奇──就像帕山迪人。
有太多事情發生。我得非常小心,非常低調。她心想。
「我同意所有費用。一個禮拜以後,我會讓我弟媳的一個女僕被解僱,妳得去申請這個職位,我相信妳有能力製造出假身分。妳被僱用之後,負責監控跟回報。我會告訴妳是否需要動用到其他服務,除非我開口,否則不准輕舉妄動,聽清楚了嗎?」
「付錢的人是您,您說了算。」利絲說,微微透露出一絲巴伏方言口音。
如果她露出口音,那也是刻意的。利絲是加絲娜認識的殺手中最精湛的一個,人們稱她為「泣血殺手」,因為被她殺害的人,眼睛都會被挖出來。雖然這個名字不是她自創的,但是卻相當合用,因為她有需要隱藏的祕密──首先,沒有人知道泣血殺手是女人。
據說泣血殺手挖掉人眼是表示根本不在乎下手對象是淺眸或深眸人。事實上,這是為了隱藏第二個祕密──利絲不想要任何人知道她殺死的屍體會有被燒焦的眼眶。
「那我走了。」利絲站起身。
加絲娜心不在焉地點點頭,又回想起先前跟靈的奇特交手。閃動的皮膚,在皮膚上舞動的顏色有如焦油。
她強迫自己暫時不再想下去。她需要專注於手邊的工作。現在,就是利絲。
利絲在門口停頓片刻,沒有立即離去。「您知道我為什麼喜歡您嗎,光主?」
「我想跟我的口袋還有它神話般的深度有關。」
利絲微笑,「當然,這點沒有必要否認,但是,您跟其他淺眸人不同。別人僱用我的時候,他們看不起整個過程。他們對於我的服務極端急切,然而通常卻絞著手、一臉輕蔑,好像很痛恨自己被逼著去做一件令人厭惡的事。」
「刺殺是令人厭惡的,利絲。倒夜壺也是。我可以敬重被僱用來做這份工作的人,卻不會去欣賞工作本身。」
利絲咧嘴一笑,推開門。
「那個新僕人,妳不是說想要讓我見識見識嗎?」加絲娜說。
「塔拉克?」利絲瞥向費德人。「噢,您是說另外一個。我幾個禮拜前把那個人賣給奴隸商人了,光主。」利絲皺眉。
「真的?我以為妳說他是妳用過最好的僕人。」
「這麼說吧,那個人太好了。颶風的詭異,那個雪諾瓦來的傢伙。」利絲明顯打了個哆嗦,然後一溜煙地出了門。
「記住我們的第一個約定。」加絲娜在她身後說。
「從來沒忘,光主。」利絲關上門,安靜地離去。
加絲娜靠回椅背,雙手在身前交握。她們的「第一個約定」是:如果有人去找利絲要訂下對加絲娜家人下手的契約,加絲娜會給予同等的報酬,換取利絲提出的人名。
利絲會這麼做。應該。其他十幾個加絲娜打過交道的殺手也會。熟客總比零賣契約來得好,而且對於利絲這種人,有個在政府裡的朋友更是好處多多。加絲娜的家人不會受到這種人的傷害,除非殺手是她自己僱用的。
加絲娜深深嘆口氣,然後站起身,想要甩掉似乎壓在肩頭上的重擔。
等等。利絲剛剛是不是說她的舊僕人是雪諾瓦人?
應該只是巧合。雪諾瓦人在北邊不常見,但偶爾還是會有。可是利絲提到了雪諾瓦人,加絲娜又在帕山迪人那裡看到一個多查一下也好,即使她因此需要回到宴會上去。今天晚上不太對勁,不只是因為她的影子跟碰到的靈。
加絲娜離開皇宮深處的小房間,回到走廊。她往上走時,上面的鼓聲倏地消失,像是樂器的弦突然被割斷。宴會為什麼這麼早結束?達利納該不會得罪了客人吧?那個人一喝酒……
帕山迪人之前對於他的失禮處處視而不見,這次想來應該也是。說實在的,加絲娜很高興她父親突然非常專注和約這件事,這表示她有空可以慢慢研究帕山迪的傳統與歷史。
她心想,該不會這麼多年來,學者們都找錯遺跡了吧?
走廊前方傳來交談的回音。
「我擔心亞須。」
「你一天到晚擔心這擔心那的。」
加絲娜停下腳步,沒有立刻上前。
「她越來越嚴重了。我們不應該變得更嚴重的。我有變得更嚴重嗎?我覺得我變得更嚴重了。」第一個聲音不斷地說。
「閉嘴。」
「這整件事不對。我們做得不對。那東西配戴著主上的碎刃,我們不該讓他保留那把碎刃,他──」
兩個人走過加絲娜面前的路口,他們是西邊來的大使,包括臉上有白色胎記的亞西須人。還是那是疤痕?兩人之中比較矮的那個──有可能是雅烈席人──一注意到加絲娜便立刻住口,叫了一聲,快速離開。
穿著一身黑銀的亞西須人停下腳步,上下打量她一番,皺著眉。
「宴會已經結束了嗎?」加絲娜在走廊另一頭問。她的弟弟邀了這兩人以及科林納城裡的每名外國使節前來參加慶典。
「對。」男子說。
他的注視讓她很不自在,但她仍然繼續往前。我應該調查一下這兩個人,她心想。她當然已經調查過他們的背景,結果並沒有什麼奇怪之處。他們之前是在講碎刃嗎?
「快點!」矮子說,回過身來拉著高男子的手臂。
高個子允許自己被拉走。加絲娜走到走廊交叉的地方,看著他們離去。
尖叫聲突然炸開。糟了……加絲娜一驚,立刻轉身,抓起裙襬跑得飛快,腦海裡閃過十幾種不同的災難。今天這樣諸事不順的夜晚,有站起來的影子還有一臉懷疑地看著她的父親,還會發生什麼事?她懷著緊繃到極點的心情,來到台階,開始拾級向上。
這一段路走得太久。她一路上聽到尖叫頻傳,爬到樓層時,迎面淨是混亂場景,一邊都是屍體,另一邊是被破壞的牆。怎麼……
破壞的殘破痕跡一路通向她父親的房間。
整個皇宮晃動,她父親房間的方向傳來碎裂聲。
不,不,不!
她跑過劃入牆壁的碎刃劍痕。
不要啊。
燒焦眼睛的屍體四散在地面,像是晚餐桌上隨意亂丟的骨頭。
怎麼會這樣。
破碎的門。她父親的住所。加絲娜停在門口,瞠目結舌。
控制自己,控制……
她不行。現在不行。她慌亂地衝入室內,雖然碎刃師隨隨便便就能殺了她,但她無法冷靜。她應該找到能幫忙的人。達利納?他一定已經喝醉了。那要找薩迪雅司。
房間看起來像是被暴風席捲過,到處都是碎裂的家具與木屑,陽台門被往外撞開、破裂,有人正朝門口跌跌撞撞地撲去,一個穿著她父親碎甲的人。是他的護衛提瑞姆嗎?
不對。頭盔破了。不是提瑞姆。是加維拉。陽台上有人尖叫。
「父親!」加絲娜大叫。加維拉踩上陽台的腳步瞬間遲疑,回頭看她。
陽台在他腳下崩裂。
加絲娜尖叫,衝過房間,撲向破碎的陽台,跪倒在邊緣。狂風扯鬆她的髮髻,髮絲飄揚在風中,她看著兩人往下墜落。
她的父親,還有宴會裡穿白衣的雪諾瓦人。
雪諾瓦人散發著白光。他撞上牆,翻滾,停止,又站起來,居然還停在皇宮外牆的牆頭,沒有摔倒。這不合邏輯。
他轉身,一步步走向她父親。
加絲娜目不轉睛,全身如墜冰窖,無助地看著殺手走到她父親身邊,跪倒在他身旁。
眼淚順著她的下巴滑落,被風吹走。他在那裡幹什麼?她看不清楚。
當殺手離開時,留下她父親被木頭貫穿的屍體。他死了──沒錯,他的碎刃出現在他身邊,持劍者死去時向來如此。
「我這麼努力……」加絲娜茫然地低語。「我做了這麼多事,就是為了保護他們……」
怎麼會?利絲,是利絲幹的!
不對。加絲娜沒想清楚。那個雪諾瓦人……她不會承認擁有這個人,她把他賣了。
「我們對於妳的損失深表遺憾。」
加絲娜轉身,眨著滿是淚水的雙眼。三名帕山迪人,站在門口,穿著他們各具特色的服裝:縫紉整齊的布料外袍,腰間綁布帶,無袖寬鬆襯衫,寬鬆大敞的背心兩側也有開口,以鮮豔的顏色織成。他們的衣服沒有性別差異,不過她認為差別在於階級不同,那麼──
夠了,她對自己說,就這麼他颶風的一天,別老像個學者那樣思考可以嗎!
「我們為他的死負責。」站在最前面的帕山迪人甘納說,她是女性,但是帕山迪人的性別特徵似乎差異不大。衣服掩飾住胸部與臀部原本就不明顯的曲線,幸好沒有鬍子是一個明確的特徵。她見過的所有帕山迪男人都有鬍子,上面會有寶石裝飾還有──
夠了。
「妳說什麼?」加絲娜質問,強迫自己站起。「甘納,為什麼說是你們的錯?」
「殺手是我們僱用的。妳父親是我們殺死的,加絲娜.科林。」帕山迪女人以宛如吟唱般起伏的濃重口音說。
「你們……」
她滿腔情緒瞬間變冷,宛如在高山上凍結的河流。加絲娜看向甘納,然後是克雷德,最後是伐納利。三人都是長老,帕山迪統治議會的成員。
「為什麼?」加絲娜低語。
「必須如此。」甘納說。
「為什麼?」加絲娜向前一步,厲聲質問。「他為你們戰鬥!他讓野獸不去襲擊你們!你們這群禽獸不如的東西,我父親想要跟你們和平共存!你們為什麼挑這個時候背叛我們?」
甘納抿起嘴唇,聲音的旋音改變,像個母親在向幼小的孩子解釋難懂的事情。「因為妳父親即將要做出一件很危險的事。」
「叫達利納光爵來!」大廳外的一個聲音大喊。「颶風的!我的命令傳到艾洛卡那邊的人了沒?帶太子去安全的地方!」藩王薩迪雅司帶著一群士兵闖進房間,肥胖通紅的臉龐滿是大汗,身上穿著加維拉的衣服,代表王權的尊貴服飾。「這些野蠻人在這裡幹什麼?颶風的!保護加絲娜公主。做出這種事情的人是他們的隨從!」
士兵上前包圍帕山迪人。加絲娜不理他們,轉身回到破碎的門口,一手扶著牆,低頭看著她父親仰躺在下面的岩石上,碎刃在他身邊。
「我們會開戰。我不會阻止戰爭發生。」她低語。
「我們明白。」甘納從她身後說。
「那個殺手。他走在牆壁上。」加絲娜說。
甘納什麼都沒回應。
加絲娜的世界碎裂的同時,她捕捉到這塊碎片。她今天晚上見到了不尋常的事情,不應該會發生的事情。跟那奇怪的靈有關嗎?跟她在玻璃珠跟黑色天空世界的經歷有關嗎?
這些問題成為她保持鎮定的生命線。薩迪雅司質問帕山迪領袖們,但得不到答案。他站到她身邊,看到下方的慘劇時,宛如酒醉般連連後退,大喊要侍衛跟上,立刻衝下去找斃命的國王。
幾個小時以後,他們發現刺殺行動以及三名帕山迪領袖的投降,掩護了大多數帕山迪人的逃逸。他們飛快地逃離城市,達利納派去追他們的騎兵也被殲滅。上百匹馬,每匹幾乎都是無價之寶,跟騎士們一起喪命。
帕山迪領袖們什麼都沒說,沒有給予任何線索,直到他們因為犯下的罪行而被吊死。
加絲娜無視這一切。她將精力放在盤問倖存的守衛身上,詰問他們看到了什麼。她追查所有關於這名如今惡名昭彰的殺手的消息,並試圖從利絲那裡挖取情報。
但利絲幾乎什麼都不知道,她擁有他的時間很短,宣稱對於他奇怪的力量並不知情。加絲娜找不到他的再上一任主人。
接下來就是閱讀。專心、瘋狂的研究,讓她不去多想她失去了什麼。
那天晚上,加絲娜看到了不可能的事情。
她會找出來那到底是什麼。
|